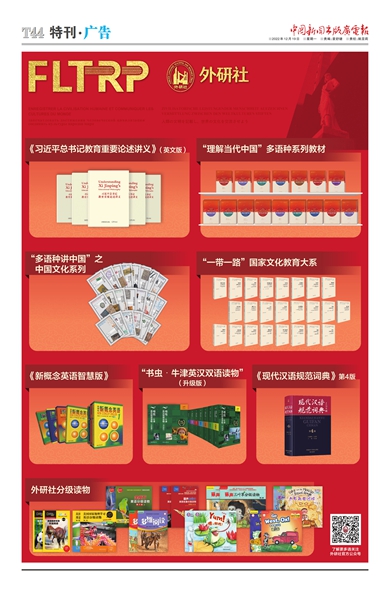高质量打造国家级重大出版项目
――《全辽金元笔记》编辑手记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2-12-19

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强调了“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明确提出“提升古籍工作质量”,从提高古籍保护水平、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三方面进行了部署,为古籍学科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指明了路径。特别是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大象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在文献类图书规划和出版方面深耕细作,特别是在古籍文献整理方面,有“历代笔记文献丛刊”宏大出版项目。出色完成出版的《全宋笔记》,在学术界获得极好评价,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全宋笔记》的出版,为出版社积累了丰富的大型古籍整理图书策划和出版的成功经验,也锻炼出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编辑人才。大象出版社正在有序推进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全辽金元笔记》,就充分借鉴了《全宋笔记》的成功经验。同时,出版社也配备了专业且数量足够的编辑力量以保证该项目的学术质量,努力打造又一标志性的国家级重大出版项目。
作为大象出版社的一名社科类图书编辑,笔者非常荣幸能进入《全辽金元笔记》丛书编辑组,负责第一辑其中一卷的责编工作。在这项巨大的挑战中,笔者不仅积累了初步的古籍整理经验,也体会到了新时代做大型古籍整理文献的要求,总结了项目经验。现就《全辽金元笔记》项目编校过程中的感受与收获分享一二,以供同仁参考与批评。
了解项目来龙去脉
《全辽金元笔记》是辽金元笔记文献之汇辑整理,汇编、校点全部现存辽金元三代笔记文献。根据课题组对辽金元笔记的界定,所谓笔记,指那些没有严格体例、信笔记录摘录而成的著述,是古代文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蕴含大量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经课题组排查确定,存世辽金元三代笔记计286种903卷,预计编为4辑,暂定每辑10册,共约40册,收录辽金笔记17种,元代笔记269种,总规模预计1000万字。
2019年8月28日,大象出版社举行了项目启动会,项目组编辑成员全体参与。在会上,笔者了解了《全辽金元笔记》项目的整体构思、学术价值,以及对项目参与者的总体要求,并与课题组成员一起逐条学习和讨论了该项目的《凡例》《工作流程》《校点中一些事项的说明》等会议材料。在各位老师针对项目定位、时间节点、编写体例、工作重点、工作难度及流程的交流、讨论中,笔者知道了项目的来龙去脉,对将要编辑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为后期的编辑加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编辑难度非一般书可比
项目组为保证质量与进度,采取各种措施,如建立稳定、专业的项目团队,对组员进行扎实的古籍整理专业培训,制定并执行严格的工作流程等。虽然如此,在编校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受到《全辽金元笔记》的编辑难度仍非一般学术图书可比。
首先,整理难度极大。以笔者所负责的一卷为例,收录10种辽金元笔记,其中《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文辨》《滹南诗话》4种有整理成果可借鉴;《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屏山李先生鸣道集说》两种所用底本为手抄本,且未经整理过,内容还涉及大量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知识;《辽志》《金国志》《辽东志略》《佩楚轩客谈》4种虽篇幅较短,但未经整理过,整理者给出了大量的校勘记。其内容之繁杂、文体之复杂,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岂是普通图书所能囊括?
其次,各卷体例和文字处理不统一。如笔者负责的一卷的校勘记,来稿时就没有严格按照丛书统一的校勘记书写规范进行编写。虽然项目前期已经确定了丛书体例,给出了详细的文字处理规范,但第一辑有数十位整理者和编辑共同参与,各卷情况又不尽相同,难免会有处理不一致的地方,这就加大了编辑工作的难度。
最后,大量文字录入错误问题。为了避免文字录入环节产生错误,本项目规定校点者在原书复印件上校点(统一将复印件粘贴在A3纸上,留出充分的空间作点校),出版社请专业古籍录入公司录入,最大限度减少书稿差错率。但在实际文字录入工作中,还是有大量文字录错的情况――多由繁简输入转换问题、录入人员不认识某些文字、底本文字模糊不清等原因造成,加重了编辑校对工作。
多举措解决编辑难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一是系统学习古籍整理专业知识。在《全辽金元笔记》项目编辑过程中,笔者认识到自身古籍整理经验不足,古籍整理专业知识需要补充,便主动参加了“中华书局古籍整理训练营”,系统学习并掌握了古籍整理实操工作的知识框架和基本技能。
二是借助各类工具书。工具书在文献整理工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利用好工具书可以有效提高文献整理工作的效率。除了编辑工作中常用的各类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外,笔者还学习了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陈垣《校勘学释例》等著述。《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公布后,笔者也及时找来阅读学习。为了解决底本中手写字的识别问题,参考了于右任编的《标准草书》。此外,《中国历史年表》也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三是合理使用各种网络数据库资源。相较于查阅传统纸质文献资源,通过网络数据库搜索文献资料更方便快捷。笔者在编辑工作中,对于各种笔记的参校本,大都通过网络查找各种古籍数据库获得。如通过各种文献数据库检索,发现《辽东行部志》底本使用错误,此种的校点说明中明确说“本次校点选用《藕香零拾丛书》本为底本”,但实际使用的底本为1933年重印《国学文库(第二编)》本。此种版本的封面上,虽明确提到“据‘藕香零拾’(宣统刊本每半叶十四行二十一字)重印”,实为重排本,不宜作为工作底本。笔者最终建议整理者将底本更换为《藕香零拾丛书》本。再如,《鸭江行部志》的校勘记中提到参校“贾疏本”,笔者通过知网数据库及时查到了贾敬颜的《〈鸭江行部志〉疏证稿》,以辨其引用是否正确。遇到读起来感觉不顺畅,或文意不明之处,通过读秀中外学术搜索引擎或其他学术引擎搜索查找问题,往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四是及时与各位整理者、编辑同事以及录入排版人员沟通。项目组建立了顺畅的沟通联系机制,如建立了编委通讯录,并根据工作内容需要建立了工作微信群、QQ群等,方便各方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及时沟通。对于书稿中的某些标点和校勘记,笔者无法判断其句读、出校是否科学合理时,就要与整理者及时沟通,交换意见。当某些体例、版式、文字有改动情况时,及时告知同事,最大限度保证整套书编排体例的一致性。
经过3年紧张又充实的编辑工作,笔者体会到编辑大型古籍整理文献的艰辛与繁杂,从中积累了宝贵的古籍整理经验,充分认识到大型古籍整理文献项目的出版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工程,需要参与项目的编辑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协同作战的合作意识,才能打造出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精品。
《全辽金元笔记》项目启动后,项目团队与出版社编辑团队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精审校理,编校与出版工作进展顺利,目前第一辑1―10册已经完成,今年年底即将推出。
(作者单位: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