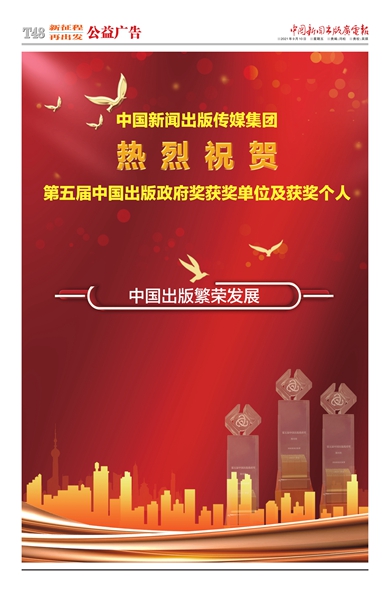《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创作中我看见一双双清澈的眼睛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1-0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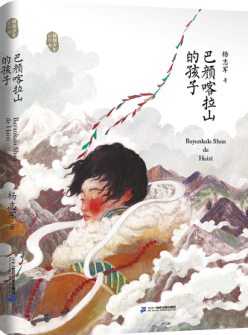
这部小说的完成,缘起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王雨婷编辑的建议。我们素昧平生,她读了我的一个3万字的中篇小说,认真写了“审读意见”,期待我修改的同时,大概也做好了被我拒绝的准备。当时我正在创作另一部长篇,欲罢不能,没时间顾及其他。但结果却是我很快放下了手头的长篇,投入到《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的创作中,因为她的“审读意见”突然诱发了我的怀旧情怀,曾经的生活里,一些我从未触碰过的人和事纷至沓来。
她的“审读意见”是这样的:
1.主角强化。虽说“我”是主人公,但目前来看,文中“我”的在场不是很多;且在关于“我”的描写中,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观看者,而不是参与者。也就是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并不多,且不具象。“我”的思想、情感和成长历程体现得不多。建议增加一些小主人公“我”的描述和故事,让“我”的存在感更强。阿爸和央金代表的是传统的原野牧人,他们的坚守和执着、韧劲和不屈,跟德吉这类旧生活的“背叛者”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我”的观点,从“我”的层面看待这些问题,力度会更大,也会更加直抵人心。比如:一些重要情节可以调整为“我”的视角,让“我”加入进来。增加“我”和央金的对手戏――“我”对央金从排斥到熟悉再到完全接受乃至崇敬的全过程。
2.童趣加强。在人物刻画、语言对话上,希望作者能使用更多符合儿童阅读的语言。可能的话,补充刻画一些藏地孩子的童年生活。目前书稿中只有“我”一个孩子,如果能有更多的孩子跟“我”互动一下,这种藏地孩子的生活图景会更加丰富具象,更有趣味性。
3.视角明确。书稿的“儿童视角”更接近“上帝视角”,“我”对于所有的真相和未参与的一些事情也非常熟知,这样似乎不符合逻辑。希望能够回到孩子的视点,作为一个6岁的孩子,有些事情是不知道的,或者是根据“我”当下的理解能力来认知来阐述这个事件,应该会更加符合孩子的视角,趣味性更强。
4.书名改为《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应该更好。
总之,瑕不掩瑜,这份书稿的整体质量非常高,我们编辑看后很是欣喜。当下小读者的阅读大部分是吃“糖”,较少涉及沉重和苦难,阅读的视野和类型也相对单一。我们的童书市场,急需这类深入生活肌理,这类关系人与自然、生命与救赎,这类关乎信念与坚守的厚重作品。我们希望杨老师能够配合做些调整,尽量让它以较完美的姿态呈现给我们的小读者,从而使他们爱上深层次的文学阅读。
于是我决定重写。启示的作用不仅在于点亮,更是一种推动。我在家里写,在飞机上写,于青岛和青海两地分别在电脑和手机上写。完成的时候又是一个夜晚,我突然想,应该记住我为什么情绪饱满地写了这样一部作品,记住一切恩典总是在不声不响中成就着你,就像星光照亮了你的夜路,等你到达目的地时,它却悄然消失了。因此多数情况下,你并不知道应该对星光说一声谢谢。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出版后,我终于可以确定地说:只有写作儿童文学,你才会面对一双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那里没有一丝杂质,没有让人猜度的阴影,没有狂风暴雨的痕迹,只有无条件的期待与信任,像灯一样照射着你。
我的儿童文学从《藏獒》开始。当许多孩子端着书,睁大无比清澈的眼睛让我签名时,我有点惶惑:为什么孩子们会喜欢我的书?之后我又写了《骆驼》和《海底隧道》,也都是事先没有刻意去为儿童写作,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童小说。
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有一种童稚烂漫的天性,能像孩子一样理解事物,有一双天然澄莹的童眸,能够躲开所有的晦暗与复杂直抵单纯。我天真地写了《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那里有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有精神境界超凡脱俗的涌现,有底线也有高标,线索清晰的表达里“我”的成长始终都在吸纳博大与力量,始终都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
在这个穷则思变的历史节点上,爱成为岩石一样坚固的存在,人与自然天衣无缝的弥合里,又有生态恶变的断裂,牧人的生存方式带着最后的告别,被原汁原味地保留在字里行间,就像一座场景和人物俱在的博物馆。尽管告别游牧的过程里,有道不尽的离情别绪,但城市毕竟是永恒的诱惑,就像书中的各姿各雅城――各姿各雅是黄河的正源,巴颜喀拉山群最著名的高峰。正是这座高峰的魅影,让游牧文化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文明的到来就像突然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境,异陌到令人惧怕,而又新奇到令人感奋。
而所有的变迁背后是永恒不变的人的境界,它如同万里雪山一样高尚而峻拔:转山祈祷是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因为只有为所有人祈求幸福,才会有自己来世的幸福。无目的而具有目的性,无功利而具有功利性,诚如老子所言:“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撒盐奶奶”的家常举动与平凡作为,不经意中成了人类精神的至高表现,就像巴颜喀拉山一样带着雪峰的清洁和源头的高贵。在如此广阔的氛围里,我和我的人物一起长大了。
写作的过程中,眼前始终闪动着一双双儿童的眼睛。我相信一双眼睛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但被拯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涤除尘霾,接受洗礼,用孩子的眼睛擦亮我的眼睛,用孩子的心灵照明我的心灵。
我今后的写作将一如既往地服从我内心的需要:在创作成人作品的同时,不放弃对儿童文学的追求。成人文学的品格会要求我尽可能大胆地面对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悲苦、生活的艰辛以及一切属于假丑恶的人类的精神垃圾,但在儿童文学里,我一定要发掘并打磨最纯净最有价值的精神钻石,置放在一任透彻的原始的蔚蓝下,吸引一双双跟钻石同样清澈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