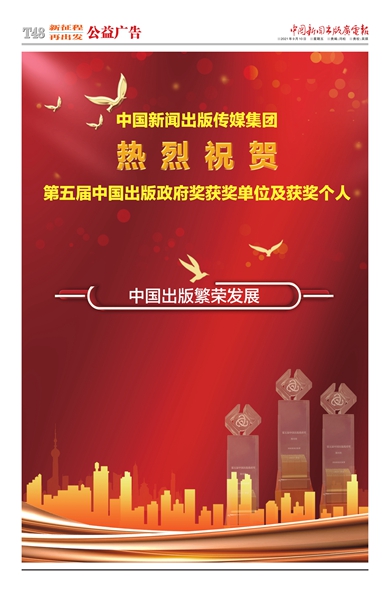《人世间》(三卷本)
梁晓声的现实主义新高度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1-0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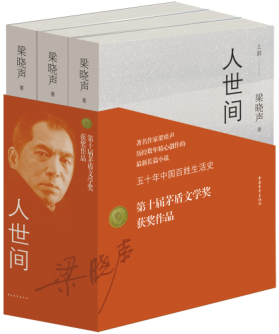
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是一部新中国的社会生活史。它把近50年的中国百姓生活直观地呈现给今天的读者,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年代写作,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而且时间越久,越能显示出不可磨灭的价值。
《人世间》极具年代感,作品从上世纪70年代初写起,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时间跨度近50年。当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与每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人间奇景。在《人世间》里,近50年出现过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工农兵上大学、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热、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动向和重要社会现象,一一得以艺术呈现,并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对小说中的各类人物产生深刻影响。
一部作品,要写好历史,必然要写活人物。在《人世间》里,有底层的下岗工人,有家庭妇女,有经商者,有民警,有知识分子,有官员,有老干部。这些人物阶层不同,形态各异,但都在经历几十年社会生活的冲刷和磨洗。
着墨最多的还是周氏家庭中的成员,尤其是哥哥周秉义。这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人物。周秉义是中国当代文学人物中非常可贵的、有可信度和感染力、真正体现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的形象。姐姐周蓉,敢做敢为,自己的命运自己扛。周蓉话不多,但极有个性和追求,尤其是在面对困境时,更彰显了中国知识女性顽强坚韧的意志品质。周秉昆身为平民子弟,具有劳动人民的美好品性。他为人正直仗义,勇于担当。他特别忠实于自己的个人感情,毅然决然与怀有他人身孕、处境艰难的郑娟结婚,勇敢挑起郑娟一家极度贫困的生活担子。普通人的善良美德和人生信念,在周秉昆身上毕现无遗。周志刚是周氏兄妹的父亲,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他的内心一直洋溢着国家主人公、社会建设者的豪迈和激情,又深明大义,通情达理。
在《人世间》中,值得品味的人物还有很多。我们从中读到了个人的成长、草根青年的奋斗,读到了婚姻家庭的千差万别,读到了家族的存续衰亡,读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亲疏远近,读到了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进步。我们还读到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读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读到了读书影响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启示。我们更读到了作者的人间情怀,读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忧思和悲悯。
梁晓声与共和国同龄。他的人生命运,天然地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一直在与时代同行,秉持着社会良知和责任,用他擅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认知。
梁晓声对这个时代充满感情,是时代的发展进步推举着他,让他不断获得观察和思考的视野和角度,更新自己的方法和路径。他进入这个时代,观察这个时代,思考这个时代。这种执着和认真,奠定了梁晓声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
梁晓声的现实主义,不回避,不躲闪,不对症结视而不见,不对问题麻木不仁,对社会和时代的责任使命,成为他观察和思考的前提。同时,梁晓声的现实主义,不矫情,不媚俗,他总是秉持着社会的良知和道义,给社会传达着正能量,希望人性能向上、向善,社会能向美、向好。梁晓声有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执着信念,而且随着阅历的丰富,这样的信念和操守,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更加密不可分,水乳交融。而这一切,他都呈现在了《人世间》里。《人世间》是梁晓声的人生阅历、文学经验和思想储备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无疑代表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
梁晓声创作的辨识度,是从他写知青小说后开始清晰起来的。《人世间》是对“好人文化观”的形象表述,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交集,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同时,《人世间》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人是这样的,但可以是那样的,应该是那样的,这是梁晓声提出“好人文化观”的前提。
在《人世间》里,作者善于挖掘人物身上所闪现的正直善良和情义担当。即便生活再艰辛,也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就是深陷困境,也要互帮互助,自立自强。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做一个好人,是对人性、人心的内在要求。社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作为人本身,越应该向善、向上、向美。当生活处在不可调解之时,总有一种正直的友善的力量,内在地驱策着生活向前推进。而矛盾的调和与解决,又往往得助于梁晓声价值取向的牵引。
梁晓声说过的四句话广为流传:“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这是他从文明、文化的角度,为“好人”定下的标准。希望人性向上向善,社会向美向好,这是梁晓声“好人文化观”的深厚内涵,也是《人世间》的深刻魅力。
《人世间》是一部留住了时间的作品,它也定然会被时间所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