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狗》:
在雪原与人心间重建自我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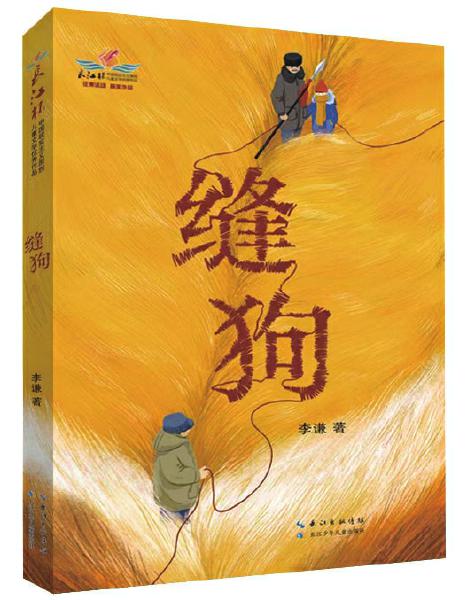
李谦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家李谦始终对东北地域文化怀着质朴深情,她注重田野调查,将地域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入儿童文学创作。其作品不仅展现出自然之美,更因融入长白山原住民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人类文化学内容而内蕴丰厚。
长篇小说《缝狗》固然具备上述特征,却也呈现出新的创作倾向。在我看来,《缝狗》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以儿童视角为棱镜,既刺破了教育规训的虚妄,又留存了成长的复杂肌理,为儿童文学如何彰显“儿童主体性”提供了珍贵范本。
尹小安的黑瞎子沟之旅,本质上是一场被功利教育规训甚至异化的儿童在自然与民间伦理中重建主体性的救赎之旅。
当今家庭及学校对“好孩子”的要求,往往被简化为“听话”“优秀”“符合标准”,这种实用性评价标准实则是成人世界对儿童主体性的隐性剥夺。尹小安初登场时,正是这种异化的典型:他的价值判断被“排名”“竞争”“面子”所绑架,澳大利亚游学资格的得失成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尺,而他对陈辰的怨恨,本质上是“输不起”的规训产物。
“蒲公英”微信群的存在,构成了功利教育的微型缩影。群里的孩子们用“宁古塔”“发配”解构黑瞎子沟之旅,将游学异化为“打卡竞赛”,本质上都是被消费主义包装的“教育商品”。尹小安最初对微信群的依赖,折射出城市儿童对虚拟社交的沉迷:他们习惯在屏幕后用表情包表达情绪,用点赞衡量友谊,在虚拟社交中塑造“人设”,却在真实冲突中形象坍塌——当大狗扑来时,尹小安下意识将林月灵挡在身前,这正是长期“自我中心”逻辑的极端显现。
与城市教育的“标准化评价”不同,黑瞎子沟的道德准则根植于生存实践:五爷的“老爷们儿”哲学——“没事不招事儿,出事儿不怕事儿”,没有华丽辞藻,却直指担当的本质;大头怒斥他“不算男生”时的暴怒,林月灵受惊吓后仍为他辩解的善良,构成了一套基于“共情”与“责任”的价值体系,这种来自同伴的真实反馈,远比课堂上的“德育课”更具说服力。
作品刻意回避了“成人拯救儿童”的俗套叙事,而是让民间伦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六爷带着大头登门和解时,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用“小哥俩拉拉手”的朴素智慧,让尹小安在羞耻中领悟“和解不是软弱”;十四爷缝狗时的专注与温柔,则在解构“动物工具论”的同时,传递出“生命平等”的哲学——当尹小安追问“大青算不算好狗”时,他已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判断善恶,而非依赖成人给定的答案。
这种主体性的唤醒体现在尹小安的行为转变中:从用恶作剧捉弄伙伴,到主动给林月灵拍掉头发上的雪;从拒绝给奶奶开门,到为五爷劈柴、喂狗;从对“寒假日志”的功利期待,到对“缝狗”“冻青”的纯粹好奇。这些变化并非源于成人的刻意教导,而是在真实的人际互动中自然生长。
优秀的儿童文学从不回避人性的幽暗,因为真实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对复杂世界的认知。《缝狗》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既写儿童的成长,也写成人的挣扎,让尹小安在观察人性复杂性的过程中完成自我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