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深情写下眷恋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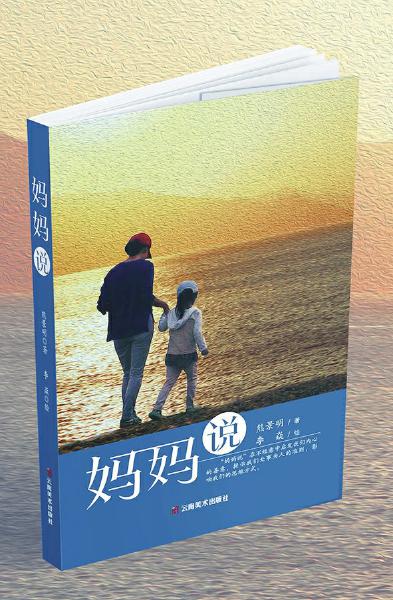
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离乡近50年后,熊景明依然保持着一口纯正的老昆明乡音;令她念念不忘的,也是老昆明的那些往事。退休以后十几年,她提笔写下了三本书:《家在云之南》《长辈的故事》《妈妈说》,每一本,都在写故乡,写故人。
妈妈,是她写下这些故事的起点。在“一席”的演讲中,熊景明讲道,当女儿成年,她终于有了写作的空闲,首先写下的,就是母亲的故事。母亲苏尔端,20世纪初出生于昆明的一户书香门第。外公苏涤新曾留学日本,是同盟会在云南的第一批会员。苏家门风严谨而氛围宽和,《长辈的故事·母亲和我》中写道:“二舅少时贪睡,外公写一首讽刺诗贴在他房门口……”这样的家庭,涵养出母亲勤谨而又幽默的气质。“有佣人侍候的日子随战乱终结,母亲写字描花的纤纤细手拿起斧头劈煤块,洗衣做饭带孩子。她一样哼着京戏,做完一件又一件家务,尽妻子和慈母的本分。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家大小穿戴利利索索。”
母亲少年时患白喉,在缺少医药的年代虽然奇迹般痊愈,却使心脏受到损伤。在40岁时,她心脏病发,此后长年卧床。卧床的母亲,依然是大家的中心。她是全家几代人的“箍桶索”,也是亲友们乐于亲近和倾诉的对象。
熊景明继承了母亲的乐观豁达与幽默。她的笔触掠过战乱的年代、困难的时节,抚过个人受制于时代的遗憾与困苦,却并不在苦难中久久停留。《长辈的故事》从“家”开始,辐射至身边走过的亲友、故人,以及他们对自我与他人的爱、责任、关怀、困惑;他们真实的情感与情绪、语言与行为,都通过她细细的描述,缓缓流出纸端,如同复活于文字中。这种真切,使得这份个人化的书写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属于时代的共同体认。
《妈妈说》里,记录了母亲对熊景明说过的各样话语,也记录了伴随这些话语的故事和语境。这里面有爱的教育,如“一句好话暖三冬”“不记隔夜仇”“人亲骨头香”,也有温柔的宽慰,如“哪个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折财免灾”……似乎再大的事情,再糟糕的情形,都可以化作一句调侃,轻轻放下。她说:“待到我自己成家,也见识了许多人的家庭后,才知道生长在一个以幽默代替责怪的家庭中有多幸运。”
从这个角度来说,《妈妈说》既是熊景明对妈妈的追念,也是她从家出发走向世界之后,对自己来时路的一次深情回望。作为通过家庭成员内部传播的非正式文本,“妈妈说”体现了一代一代中国人、中国家庭普遍认同的道理,以及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而又因为它们来自妈妈,一个家庭中爱与包容的具象化身,更加深了这种文化传播的情感属性与影响深度。
无论是《长辈的故事》,还是《妈妈说》,她写的都不是大道理。翻开书页,你看到的是“泪水先笔墨而下”的深情,是某个地方“很好很好——仅次于昆明”的眷恋,是以“一家”的故事折射一个时代的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