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藏在现实深处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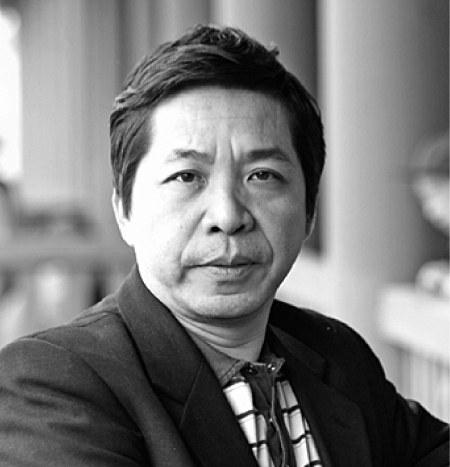
通常我们习惯将文学与想象联系在一起,将生活与真实联系在一起,其实也可以置换一下,将文学与真实联系在一起,将生活与想象联系在一起。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建构这种思维方式,让天边的一朵云,眼前的一朵花寄托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情绪。可以说自从文学产生以来,人类的想象力一直藏在现实深处,并且借助语言在发现者和欣赏者之间建立了一座心灵的桥梁。
王蒙以中国古典诗词为载体,将历史沉淀的真实情感凝练为文学意象,《诗词中国》并非单纯解析文字,而是通过诗词中的“一朵云”“一江水”等具象符号,唤醒读者对文化基因的共鸣,打捞真实的文化脉络与情感传承,借古人之诗词,让读者触摸到不同时代的生活纹理,激发对传统文化的想象。
冯骥才笔下的春节习俗是现实民俗的真实切片,《过年书》在描摹市井生活时,刻意将“年兽”“灶神”等传说元素渗透进现实场景,使“过年”这一现实行为成为集体想象的容器。作品颠覆了传统认知——现实生活因想象而获得仪式厚度,文学则因记录民俗本真而更具生命力。
在《要爱具体的人》一书中,乔叶以琐碎日常切入,将菜市场争吵、邻居叹息等“现实颗粒”升华为情感寓言。她拒绝抽象的人性探讨,转而让“皱巴巴的零钱”“阳台上晾晒的旧衣”成为爱的证据。这种“具体性”正是文学真实的体现:当现实被功利主义解构时,文学通过细节想象重构了人际关系的温度。
蔡崇达的《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以自传性笔触还原童年友谊,记忆中的石板路与蝉鸣构成真实的时空坐标系。但文中“会说话的榕树”“月光下的影子游戏”等超现实意象,暗示了现实与想象的互文——童年本真需借助文学想象才能被完整打捞。作品印证了“回忆的本质是现实的再想象”,文学在此成为修复记忆碎片的黏合剂。
在次仁罗布笔下,藏地雪山的苍茫与转经筒的嗡鸣,既是地理真实的复刻,更是精神图腾的“象征性再现”。《乌思藏风云》通过藏民朝圣、牧场迁徙等现实事件,将族群历史编织成史诗级想象,让“乌思藏”超越地域概念,成为文化认同的隐喻。
《哪吒》是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周楞伽对哪吒神话的重构,将“剔骨还父”的决绝嫁接到现代少年的身份焦虑中,在传统神话的基础上创新演绎,既有对古老神话故事真实内核的挖掘,又赋予角色和情节新的想象空间,让经典在新的想象维度中重焕生机。
文学的真实性不在于复刻现实表象,而在于捕捉事物背后的情感本质;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则需借助文学想象才能被彻底显影。当王蒙在诗词中寻找文化DNA,冯骥才用年俗重构集体记忆时,他们都在实践一种“逆向认知”——让文学成为真实的显影剂,让现实因想象而获得超越性。这些作品以文学为笔,蘸取现实的墨,在字里行间映射真实的同时,也为读者的想象开辟了广阔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