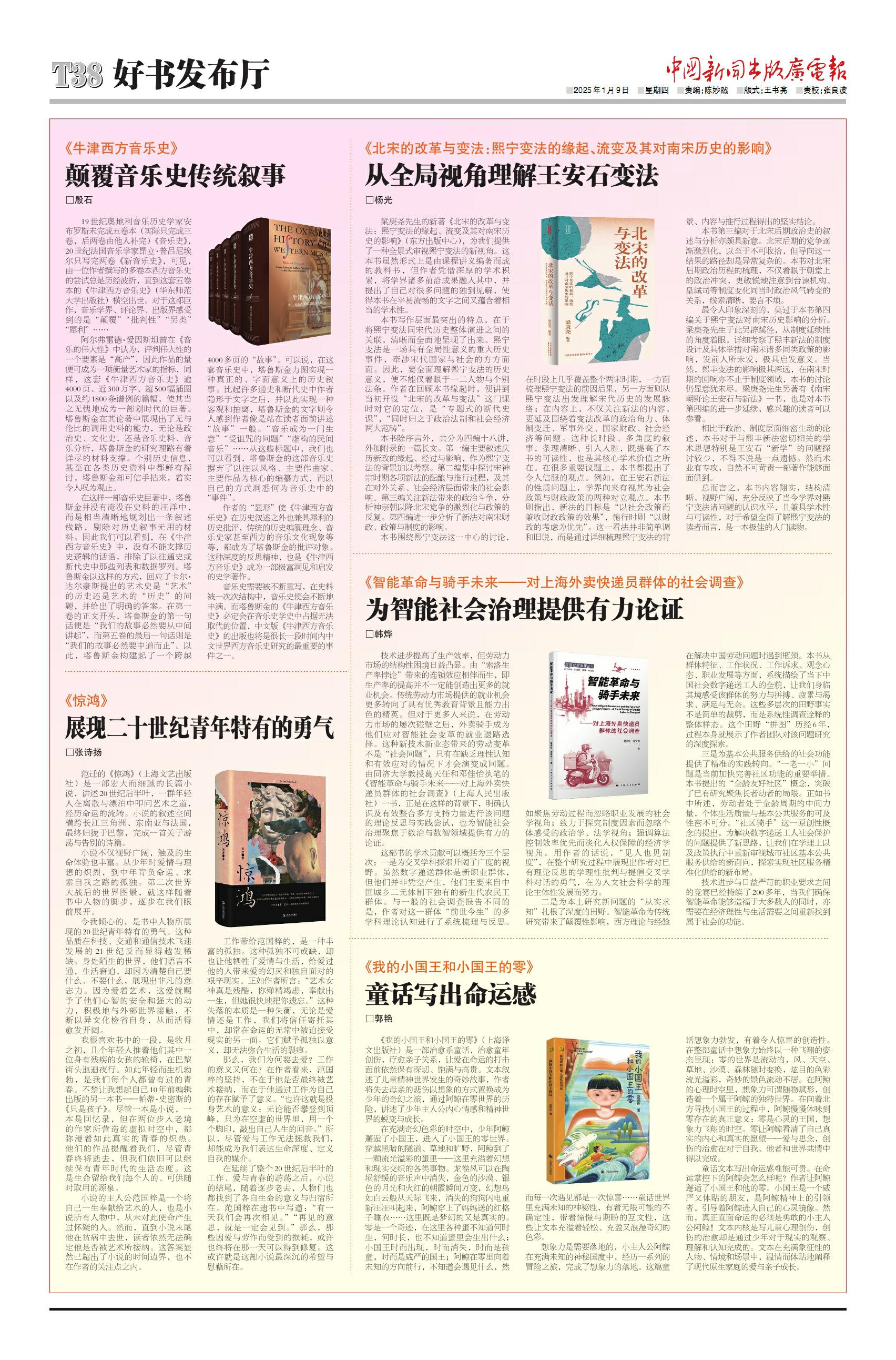《牛津西方音乐史》
颠覆音乐史传统叙事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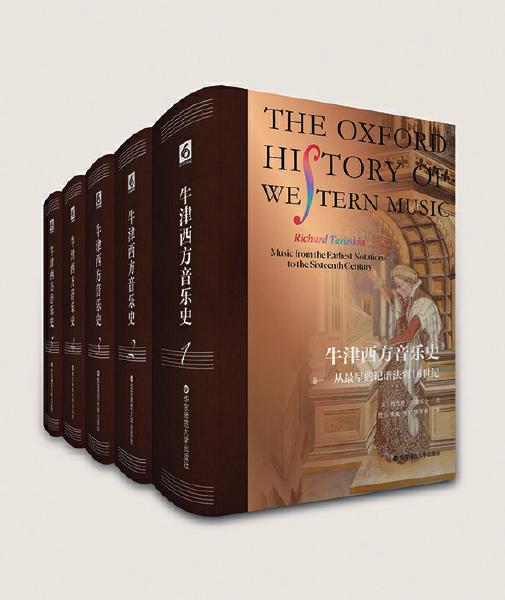
19世纪奥地利音乐历史学家安布罗斯未完成五卷本(实际只完成三卷,后两卷由他人补完)《音乐史》,20世纪法国音乐学家昂立·普吕尼埃尔只写完两卷《新音乐史》,可见,由一位作者撰写的多卷本西方音乐史的尝试总是历经波折,直到这套五卷本的《牛津西方音乐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横空出世。对于这部巨作,音乐学界、评论界、出版界感受到的是“颠覆”“批判性”“另类”“犀利”……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曾在《音乐的伟大性》中认为,评判伟大性的一个要素是“高产”,因此作品的量便可成为一项衡量艺术家的指标,同样,这套《牛津西方音乐史》逾4000页、近300万字、超500幅插图以及约1800条谱例的篇幅,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塔鲁斯金在其论著中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调用史料的能力,无论是政治史、文化史,还是音乐史料、音乐分析,塔鲁斯金的研究理路有着详尽的材料支撑。个别历史信息,甚至在各类历史资料中都鲜有探讨,塔鲁斯金却可信手拈来,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样一部音乐史巨著中,塔鲁斯金并没有淹没在史料的汪洋中,而是相当清晰地规划出一条叙述线路,剔除对历史叙事无用的材料。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牛津西方音乐史》中,没有不能支撑历史逻辑的话语,排除了以往通史或断代史中那些列表和数据罗列。塔鲁斯金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了卡尔·达尔豪斯提出的艺术史是“艺术”的历史还是艺术的“历史”的问题,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第一卷的正文开头,塔鲁斯金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的故事必然要从中间讲起”,而第五卷的最后一句话则是“我们的故事必然要中道而止”。以此,塔鲁斯金构建起了一个跨越4000多页的“故事”。可以说,在这套音乐史中,塔鲁斯金力图实现一种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历史叙事。比起许多通史和断代史中作者隐形于文字之后,并以此实现一种客观和抽离,塔鲁斯金的文字则令人感到作者像是站在读者面前讲述“故事”一般。“音乐成为一门生意”“受诅咒的问题”“虚构的民间音乐”……从这些标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塔鲁斯金的这部音乐史摒弃了以往以风格、主要作曲家、主要作品为核心的编纂方式,而以自己的方式洞悉何为音乐史中的“事件”。
作者的“显形”使《牛津西方音乐史》在历史叙述之外也兼具犀利的历史批评,传统的历史编纂理念、音乐史家甚至西方的音乐文化现象等等,都成为了塔鲁斯金的批评对象。这种深度的反思精神,也是《牛津西方音乐史》成为一部极富洞见和启发的史学著作。
音乐史需要被不断重写,在史料被一次次结构中,音乐史便会不断地丰满。而塔鲁斯金的《牛津西方音乐史》必定会在音乐史学史中占据无法取代的位置,中文版《牛津西方音乐史》的出版也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文世界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