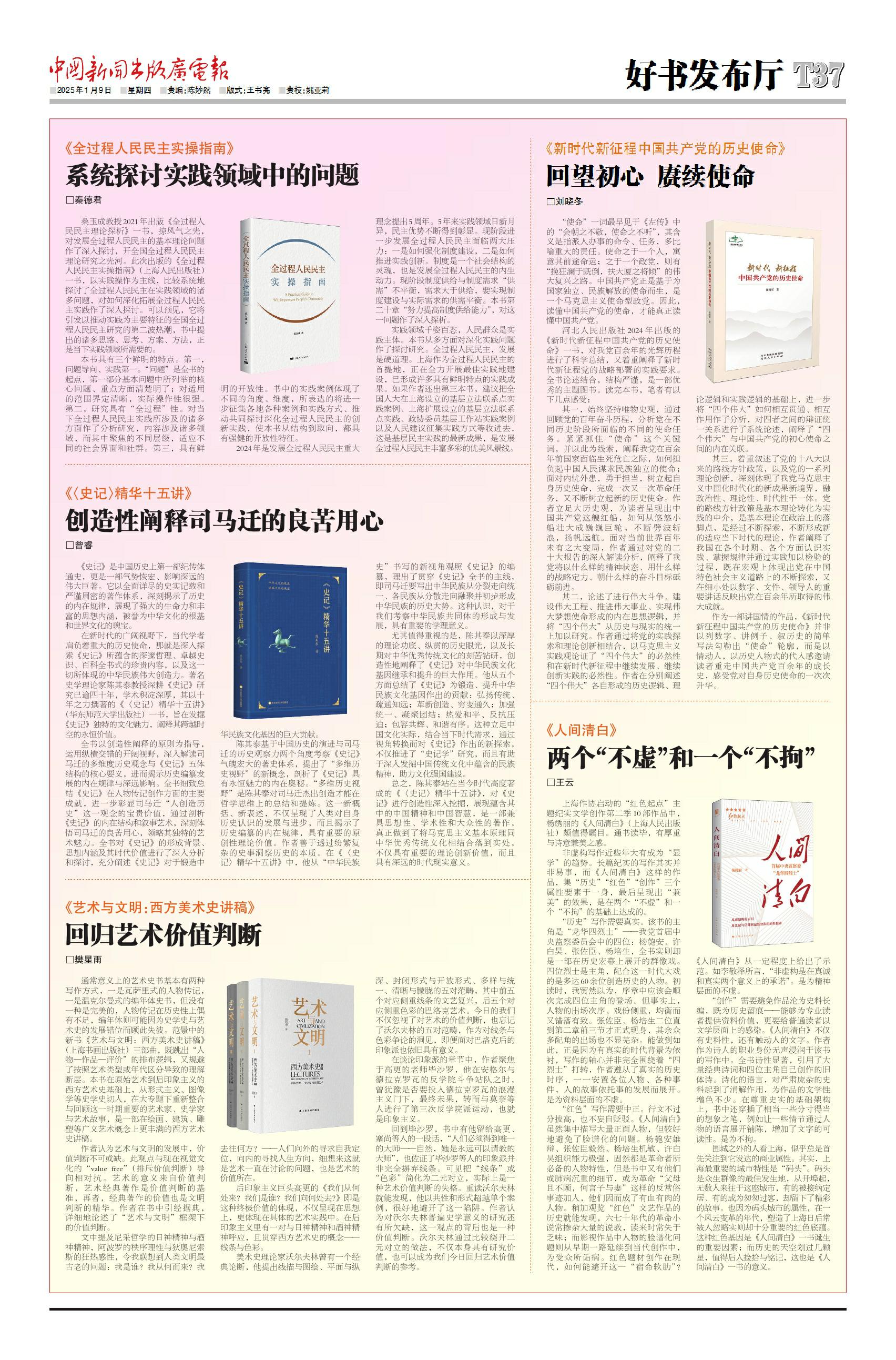-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人间清白》
两个“不虚”和一个“不拘”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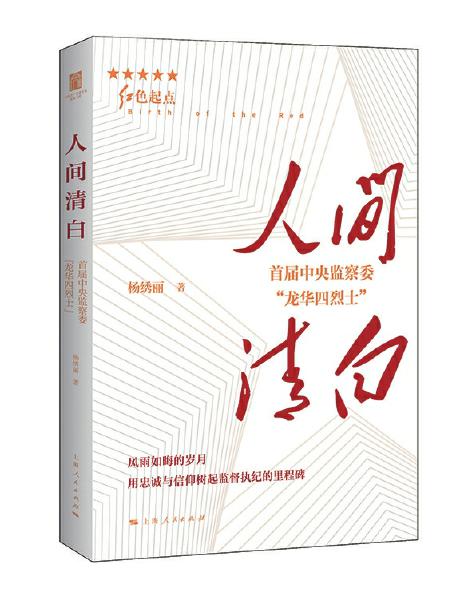
上海作协启动的“红色起点”主题纪实文学创作第二季10部作品中,杨绣丽的《人间清白》(上海人民出版社)颇值得瞩目。通书读毕,有厚重与诗意兼美之感。
非虚构写作近些年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长篇纪实的写作其实并非易事,而《人间清白》这样的作品,集“历史”“红色”“创作”三个属性要素于一身,最后呈现出“兼美”的效果,是在两个“不虚”和一个“不拘”的基础上达成的。
“历史”写作需要真实。该书的主角是“龙华四烈士”——我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四位: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杨培生,全书实则却是一部在历史宏幕上展开的群像戏。四位烈士是主角,配合这一时代大戏的是多达60余位创造历史的人物。初读时,我贸然以为,序章中应该会顺次完成四位主角的登场。但事实上,人物的出场次序、戏份侧重,均衡而又错落有致。张佐臣、杨培生二位直到第二章前三节才正式现身,其余众多配角的出场也不显芜杂。能做到如此,正是因为有真实的时代背景为依衬,写作的轴心并非完全围绕着“四烈士”打转,作者遵从了真实的历史时序,一 一安置各位人物、各种事件,人的故事依托事的发展而展开。是为资料层面的不虚。
“红色”写作需要中正。行文不过分拔高,也不妄自贬驳。《人间清白》虽然集中描写大量正面人物,但较好地避免了脸谱化的问题。杨匏安雄辩、张佐臣毅然、杨培生机敏、许白昊组织能力极强,固然都是革命者所必备的人物特性,但是书中又有他们或肺病沉重的细节,或为革命“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这样的反常俗事迹加入,他们因而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物。稍加观览“红色”文艺作品的历史就能发现,六七十年代的革命小说常掺杂大量的说教,读来时常失于乏味;而影视作品中人物的脸谱化问题则从早期一路延续到当代创作中,为受众所诟病。红色题材创作在现代,如何能避开这一“宿命软肋”?《人间清白》从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示范。如李敬泽所言,“非虚构是在真诚和真实两个意义上的承诺”。是为精神层面的不虚。
“创作”需要避免作品沦为史料长编,既为历史留痕——能够为专业读者提供资料价值,更要给普通读者以文学层面上的感染。《人间清白》不仅有史料性,还有触动人的文字。作者作为诗人的职业身份无声浸润于该书的写作中。全书诗性显著,引用了大量经典诗词和四位主角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诗化的语言,对严肃庞杂的史料起到了消解作用,为作品的文学性增色不少。在尊重史实的基础架构上,书中还穿插了相当一些分寸得当的想象之笔,例如让一些情节通过人物的语言展开铺陈,增加了文字的可读性。是为不拘。
围城之外的人看上海,似乎总是首先关注到它发达的商业属性。其实,上海最重要的城市特性是“码头”。码头是众生群像的最佳发生地,从开埠起,无数人来往于这座城市,有的被接纳定居、有的成为匆匆过客,却留下了精彩的故事。也因为码头城市的属性,在一个风云变革的年代,塑造了上海日后常被人忽略实则却十分重要的红色底蕴。这种红色基因是《人间清白》一书诞生的重要因素;而历史的天空划过几颗星,值得后人捡拾与铭记,这也是《人间清白》一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