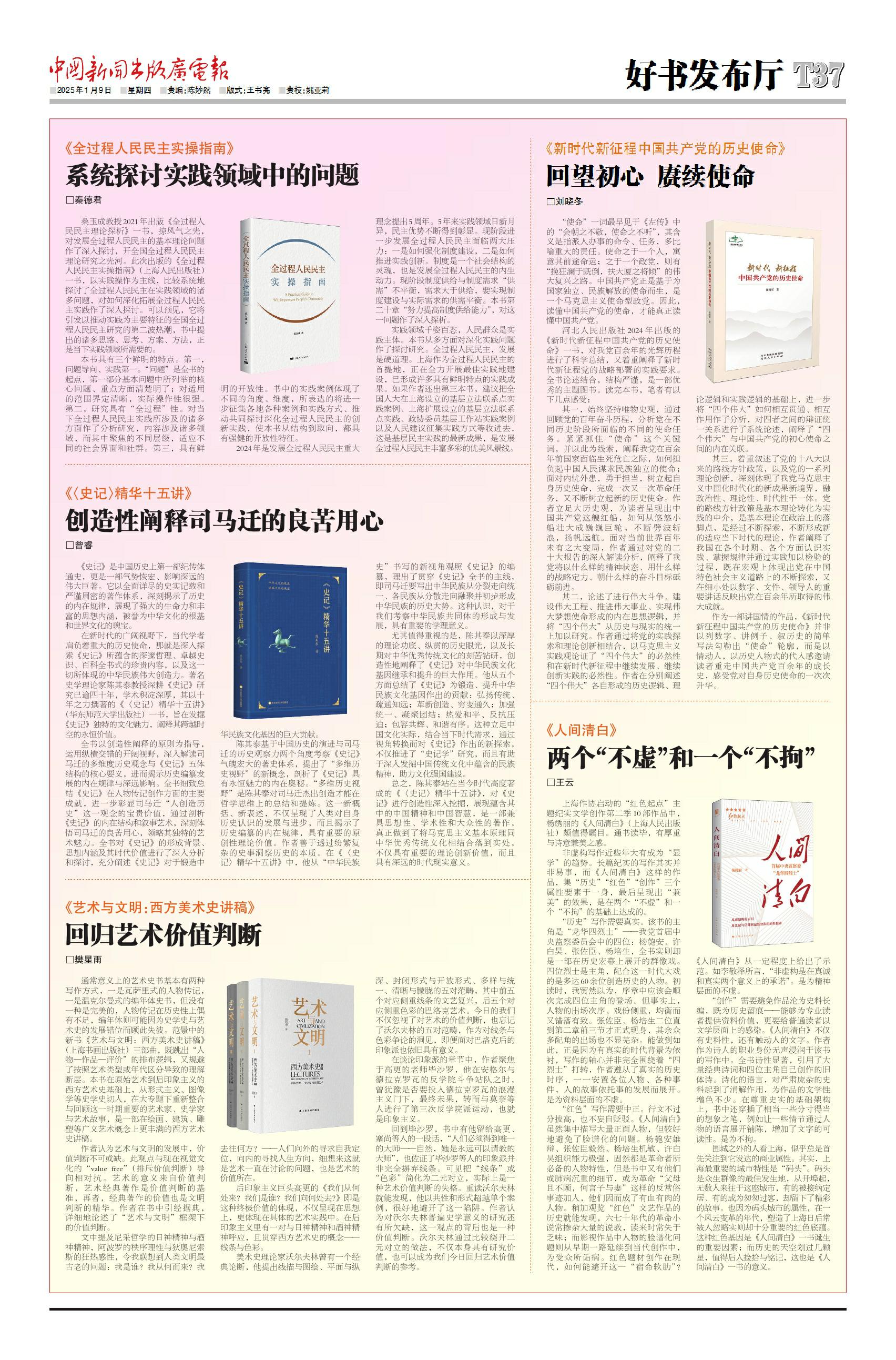《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
回归艺术价值判断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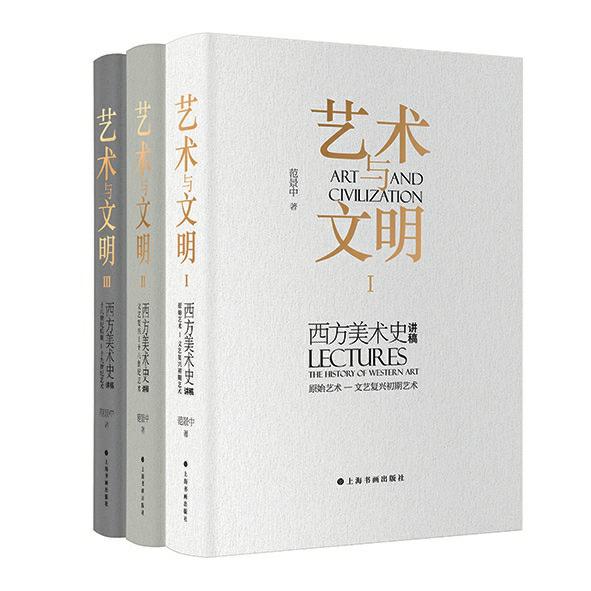
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史书基本有两种写作方式,一是瓦萨里式的人物传记,一是温克尔曼式的编年体史书,但没有一种是完美的,人物传记在历史性上偶有不足,编年体则可能因为史学史与艺术史的发展错位而顾此失彼。范景中的新书《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上海书画出版社)三部曲,既跳出“人物—作品—评价”的排布逻辑,又规避了按照艺术类型或年代区分导致的理解断层。本书在原始艺术到后印象主义的西方艺术史基础上,从形式主义、图像学等史学史切入,在大专题下重新整合与回顾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家、史学家与艺术故事,是一部在绘画、建筑、雕塑等广义艺术概念上更丰满的西方艺术史讲稿。
作者认为艺术与文明的发展中,价值判断不可或缺。此观点与现在视觉文化的“value free”(排斥价值判断)导向相对抗。艺术的意义来自价值判断,艺术经典著作是价值判断的基准,再者,经典著作的价值也是文明判断的精华。作者在书中引经据典,详细地论述了“艺术与文明”框架下的价值判断。
文中提及尼采哲学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阿波罗的秩序理性与狄奥尼索斯的狂热感性,令我联想到人类文明最古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去往何方?——人们向外的寻求自我定位,向内的寻找人生方向,细想来这就是艺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也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后印象主义巨头高更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即是这种终极价值的体现,不仅呈现在思想上,更体现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在后印象主义里有一对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呼应,且贯穿西方艺术史的概念——线条与色彩。
美术史理论家沃尔夫林曾有一个经典论断,他提出线描与图绘、平面与纵深、封闭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与统一、清晰与朦胧的五对范畴,其中前五个对应侧重线条的文艺复兴,后五个对应侧重色彩的巴洛克艺术。今日的我们不仅忽视了对艺术的价值判断,也忘记了沃尔夫林的五对范畴,作为对线条与色彩争论的洞见,即便面对巴洛克后的印象派也依旧具有意义。
在谈论印象派的章节中,作者聚焦于高更的老师毕沙罗,他在安格尔与德拉克罗瓦的反学院斗争站队之时,曾犹豫是否要投入德拉克罗瓦的浪漫主义门下,最终未果,转而与莫奈等人进行了第三次反学院派运动,也就是印象主义。
回到毕沙罗,书中有他留给高更、塞尚等人的一段话,“人们必须得到唯一的大师——自然,她是永远可以请教的大师”,也佐证了毕沙罗等人的印象派并非完全摒弃线条。可见把“线条”或“色彩”简化为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艺术价值判断的失格。重读沃尔夫林就能发现,他以共性和形式超越单个案例,很好地避开了这一陷阱。作者认为对沃尔夫林普遍史学意义的研究还有所欠缺,这一观点的背后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沃尔夫林通过比较绕开二元对立的做法,不仅本身具有研究价值,也可以成为我们今日回归艺术价值判断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