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细微之处凝神注目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3-0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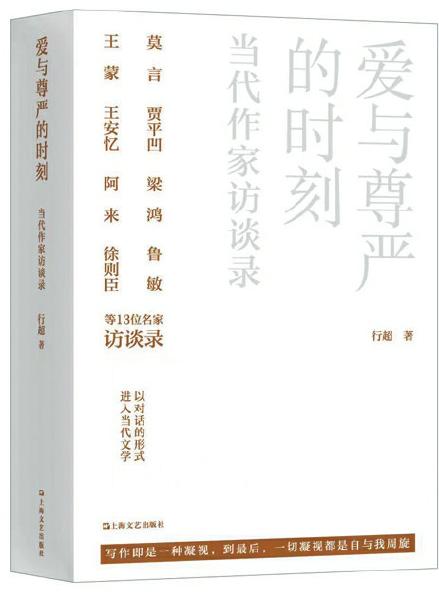
关于作家访谈,我想到一个细节,《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记者问聂鲁达:“鸽子和吉他各自代表什么?”聂鲁达回答:“鸽子代表鸽子,吉他代表一种叫作吉他的乐器。”与作家对谈,尤其对名作家提问,许多时候都需要大量知识准备、一些提问技巧,甚至还需有被反诘的勇气。在文化记者行超的《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里,我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诚恳克制的提问立场、始终如一的审美标准、对文学伦理的关切与坚守。
这本书里的访谈对象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代文学现场熠熠闪光的名字,如王蒙、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阿来等;一类是正处在创作繁盛期的中青年作家,如梁鸿、徐则臣、鲁敏、葛亮、张悦然等。对于前辈作家,行超在提问中尤为关注作家作品与时代的关系;对于“70后”“80后”作家,她更为关注个体创作的发生学与流变史。因此这本书以媒体采访的视角,为当代文学保留了一些关乎作家创作习性与审美偏向、关乎文学现场与历史进程、关于文学与时代及人之本质关系的一个个切面。在这些切面之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王蒙老而弥坚的宏阔、莫言这位“讲故事的人”的机敏、阿来对土地自然的深情、王安忆文字的洗练精准,也能看到梁鸿如何在书写中与故乡和解,周晓枫如何以写作实现对生活的突围,葛亮如何将漂泊行旅的“他城”建构为文学的“我城”,诸如此类。对不同作家,行超都秉持在场的精神,时而隐现,时而发声,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内在激情召唤访谈对象,于是作家们纷纷向她敞开心扉,谈论人生、创作、历史、自我,也对自身创作中习焉不察之处进行审视与回顾。这样诚挚的交流,让那些曾在作品中打动人的品质再度浮现,文学的历史性、在场感、鲜活性此刻并存为一体,这就是这本访谈录所展现出的动人时刻。
这本访谈录尤为难得的一点是,行超的提问最终都让作家在谈论中重返自身、重返文学的河流,作家们也借她之问重新回顾、定义,甚至校准自己与文学的关系,因此这本访谈录中的“金句”格外丰富,比如,阿来谈论自己的文学观:“我的每一部作品不是想告诉别人我在想什么,而是我对于自己心中迷惑的解答。所以文学也是一个自己认知世界、认知现实、认知历史的工具。”周晓枫谈论写作的突围:“写作要一次次逼迫自己走到极限,才能把原来的直径变为半径,才能从新的原点出发画出更大的弧。”
文学气质与人的精神性格相关,行超的文字世界里有一种风格学意义上的刚健笃实。得益于雄奇壮阔的太行山的滋养,她的文风有一种辽阔和质拙,这份“拙”,其实就是“记事、析理”的简约平直,有其深刻的文化根脉。无论是从重返90年代的日常生活书写到对当下青年创作的诸种问题探讨,抑或从回乡记的散文里凝视故土与亲人,她的文章就事论事,对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正面强攻”,而在文学访谈和散文中则轻盈、自由又深情,一边回顾文学的精神来路,一边追问文学与时代之中的人的具体而微的关系。作为读者,行超的文字,打动我的从来都是一种凝视感——对时间的凝视,对文学细微之处凝神屏息注目。因这份持久的凝视和注目,她更为在意文本背后那些永恒而确定性的存在。
(《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 行超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