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然万物书写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1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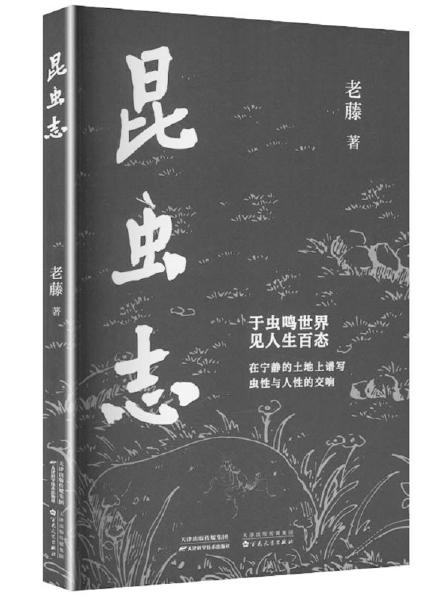
继《草木志》之后,老藤又出版了《昆虫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按照老藤的说法,写完草木之后,必须再写昆虫,这样草木才能完整。这其实映现的恰恰是作家的整体生态观。作为生态文学的典型样本,这两部小说分别以草木和昆虫为线索贯通全文,但老藤并非是将草木和昆虫用作可有可无的插叙背景,其本身即是作品的核心内容,承载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整体生态观念指引下,老藤以艺术的想象力帮助草木和昆虫重塑了灵魂,令其从故事的背景板转为主动的诉说者,从而展现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和珍视。
《昆虫志》着重描写了萤火虫、蓝蜻蜓、兰花螳螂、战神大兜、沙牛、斑透翅蝉、蜜蚁、黑蝴蝶8种昆虫,每种昆虫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隐秘的生活。以不同昆虫为题的每段情节如同藕节,既各自独立又浑然天成地生长在一起,情感隐藏在其中,如细密绵延的藕丝,连缀起主人公魏征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在小说中,昆虫不再是静默的布景,而有了自我的秉性,相应地,有了昆虫的映照,人物也真正地丰富和生动起来,找到了自我的镜像,通过这样的双向勾连,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紧密联系,从而赋予了整个故事更丰富的层次感及更深邃的意涵。
《昆虫志》的故事发生地仍然是东北,东北可以视为老藤小说的情感地理。纵观老藤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何种题材,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蕴藏着独特的东北地缘美学密码,在《北爱》《北地》《北障》《战国红》《刀兵过》等一系列作品中,老藤对东北的工业振兴、山林猎捕文化、村庄乡贤文化等主题进行了文学聚焦,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建构的是一个宏大又不失深沉的新东北生态审美场。《草木志》和《昆虫志》围绕其中的自然生态版图,将草木和昆虫作为主体纳入到审美活动中,为这一新东北生态美学景观增添了一缕自然的、本真的气息。在此意义上,当人保持对草木和昆虫的热爱和敬畏,也就获得了一种自我定位与自我认同的基础,从而具备了脱离自我无所依状态的潜在可能,这或许正是老藤为草木昆虫乃至自然万物书写的目的。
《昆虫志》仍然延续着老藤所秉持的“中和”的创作理念,强调顺其自然、恰到好处的平衡状态,这一哲学理念渗透进他对魏征这一人物形象的书写中,赋予其作品一种深沉却不失温和的特质。在情感策略上,老藤表现出含而不露的节制,恰当的节制非但不会弱化力度,反而使情感更显深沉。《昆虫志》的“中和”式美学追求,使老藤并不匆忙地对主人公的人生哲学作出是好是坏的评判,而是力求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正视精进有为精神的同时,也呼唤着顺其自然的人生姿态,这正如那些草木、昆虫所构成的世界——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