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七夕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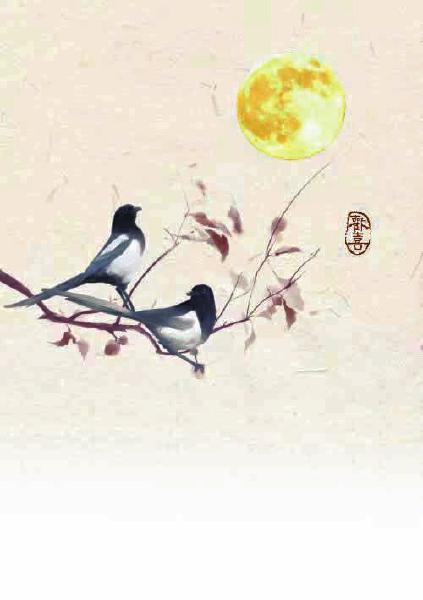
七夕前几天,天擦黑时母亲总搬竹椅到老院的梧桐树下,手里攥着半拉没绣完的枕套。浅青色的缎面上,牛郎织女隔着片云对望着,针脚有的密有的疏——都是她白天洗了衣裳、做了饭,挤着空一针一针缝出来的。父亲坐在旁边石凳上择菜,眼梢却老往母亲的绣绷上瞟,手指在围裙上蹭来蹭去,活像个藏着心事的半大孩子。
我这才记起来,父母结婚三十多年,从没正儿八经过过七夕。早先父亲在镇上农机厂上班,母亲守着家里三亩薄田,日子过得就像院角那口老井,没什么波澜,却扎实。七夕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农忙间隙翻日历偶然瞅见的俩字,远不如“芒种”“霜降”这些节气顶用。直到去年父亲退了休,家里节奏才慢下来,母亲倒捡回了年轻时爱做的针线活,父亲也学着在平常日子里找点儿乐子。
七夕那天清早,父亲起得特别早。我隔着窗纱看见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竟翻出母亲前年织的蓝布口袋,从里面小心地摸出个小布包。那是他上个月去县城赶集买的玉坠,水滴形的白玉,拴着红绳,人家说能保平安。他把玉坠放在掌心里搓了好一会儿,又怕沾了灰,用衣角擦了又擦,才揣进上衣内袋,嘴角的皱纹都松展开了。
母亲还是跟往常一样做早饭,铁锅在灶台上烧得嗞嗞响,她往粥里撒了把红枣,还多蒸了俩白面馒头——父亲最爱吃这个。父亲在灶台边磨磨蹭蹭,一会儿递块抹布,一会儿帮着添把柴火,好几次想开口,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直到母亲把粥盛进粗瓷碗,他才像是下了决心,从内袋里掏出那个小布包,往母亲手里塞:“前阵子赶集看见有人卖这个,想着你戴能好看。”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低头盯着掌心里的玉坠。阳光从梧桐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她鬓角的白头发上,倒显出些软和的光。她没吭声,就用指腹来回蹭着玉坠的边儿,过了好一会儿才抬头,眼角有点儿湿,却故意撇着嘴说:“都这把年纪了,还买这些没用的,不如买点肉回来包饺子。”嘴上这么说,手里却把玉坠攥得紧,仔细系在脖子上,又对着穿衣镜照了照,嘴角的笑压根藏不住。
午饭过后,母亲又搬竹椅到院子里绣枕套,父亲在旁边修剪月季。他把开得最红最艳的两朵剪下来,找了个玻璃瓶插上,搁在母亲手边的石桌上。母亲抬头看了他一眼,拿起绣花针,在牛郎的衣摆那儿多绣了朵小小的月季,针脚比之前密了不少。太阳快落山时,天边染了层淡淡的晚霞,父亲搬了张小板凳坐在母亲旁边,俩人就着余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从年轻时的旧事说到邻居家的杂事,偶尔不说话也不别扭,就剩风刮过梧桐叶的声儿。
晚饭时,母亲特意煮了汤圆,芝麻馅的,是父亲爱吃的。她舀了一碗递过去,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以前总听人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年轻那会儿不懂,现在才明白,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过出来的。”父亲接过碗,舀了个汤圆放进嘴里,点点头没说话,却把碗里最大的那个汤圆夹给了母亲。
天越来越黑,院子里的灯亮了,昏黄的光落在母亲脖子上的玉坠上,泛着温温的光。她把绣绷收起来,没绣完的枕套叠好放进竹篮,父亲就起身收拾碗筷。俩人并肩走进厨房,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一块儿,倒像极了枕套上那对隔着云雾相望的牛郎织女——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温柔。
我站在窗边看着这光景,忽然懂了,父母的七夕从来不是啥浪漫的仪式,是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惦记,是一针一线里的心意,是过了这么多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明白对方的默契。就像老辈人念的那句“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他们的感情没有花哨的话,却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发出了最动人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