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高额判赔重塑影视版权保护格局
——从《狂飙》案看短视频侵权治理新趋势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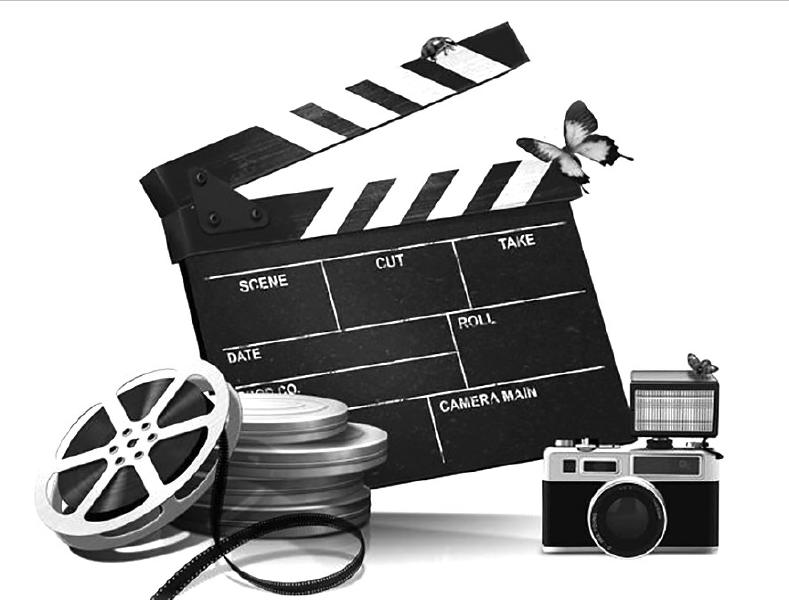
资料图片
当前,时下热播的影视、赛事等长视频内容刚一上线,就会被许多用户以切条、解说甚至直播等各种方式搬运至短视频平台。未经授权直接“搬走”的方式分走了正版影视作品本该拥有的流量,破坏了影视行业健康生态,最终透支的是整个影视创作行业的未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视版权方即使赢得诉讼,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补偿。一方面,短视频平台以合理使用与“避风港原则”等理由为自身辩解;另一方面,流量的损失难以精确计算,法院最终往往以适用上限较低的法定赔偿作出判决。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陆续出现部分影视版权裁判逐步破除行业坚冰,以高额的判赔显示出司法机关坚决打击侵权的强硬态度。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通中院)就《狂飙》案作出判决,认定某短视频公司侵权所获收益已超过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应适用裁量性赔偿,判决全额支持A公司3000万元的诉请金额。被告一审上诉以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笔者以此案为分析对象,探讨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纠纷中平台版权侵权的认定、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这两个关键问题。
合理使用无法成为平台避风港
《狂飙》案的基本案情与以往的短视频版权侵权类似。电视剧热播期间,原告A公司发现被告短视频平台设置了“狂飙”话题。截至2023年3月5日,“狂飙”话题下作品达45.3万个,累计播放量116亿次。同时,平台“热门”和“分类”栏目中设有影视专区,包含《狂飙》直播回放选项,取证直播及回访共1100个,总观看量超40万人次。A公司遂向南通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某短视频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合理费用共计3000万元。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短视频平台对用户侵权行为构成应知,未采取必要措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并全额支持了A公司3000万元的诉请金额。
该案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的认定。如前所述,短视频平台一般的抗辩思路包含两个要点:一是用户上传的短视频属于“二创”作品,构成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平台自然也不必对其承担责任;二是即使用户行为构成侵权,平台对其也不知情,并且在收到投诉、起诉材料后已经采取了删除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不应当承担责任。然而,事实上这两点抗辩在大多数短视频侵权案件中都不成立。
首先,平台上针对热播影视剧制作的短视频很难构成合理使用。热播影视短视频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切条搬运等复制类短视频,以及介绍、评论、戏仿、鬼畜等“二创”类短视频。切条视频一般是将影视长视频直接切割成若干连续的片段分别上传至平台,有的甚至还制作成合集的形式,以实现让观众在平台完整地观看影视剧集的效果。还有一类切条视频只对原视频中的精彩镜头进行集锦剪辑。
基于介绍、评论、戏仿、鬼畜等行为所产生的短视频往往被短视频平台称之为“二创”类短视频。具有独创性的“二创”类短视频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从情形上看,这些“二创”类短视频存在“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情况,可能符合合理使用的场景。然而,“适当引用”后创作的新作品,必须区别于原作、独立于原作,同时在引用比例上存在限制。引用比例的“适当”不仅仅包含了量的要素,也包含了质的要素。从影视作品制作角度来说,关键镜头和重点内容的拍摄耗费了更多的心血与经费,“高潮”部分往往是内容最为重要、最吸引观众欣赏作品的主力,观众在短视频中获取了该部分精彩镜头以后,很大可能就满足了需求,放弃了欣赏原作品的计划。因此,“二创”类短视频引用了“关键”镜头和重点内容,即使引用比重较低,且/或增添了评论部分,也不属于适当引用,不能以合理使用作为抗辩理由,拒绝承担侵权责任。
具体到《狂飙》案中,侵权用户不仅上传了影视剧集片段,甚至还提供了《狂飙》的直播及回放,侵权属性一目了然。南通中院对此指出,案涉短视频对原作品部分内容具有替代性,已经超出了合理使用范围,构成侵权。
其次,平台设置热播影视话题、影视专区等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基于对“避风港原则”的错误理解,部分平台经常认为只要将版权人投诉的侵权链接删除或屏蔽,就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然而,《民法典》对于必要措施的规定是开放式的,既包括收到通知后删除侵权链接的消极必要措施,也包括制止重复侵权、建立预防机制等积极必要措施。《狂飙》案的主审法官强调,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是否必要,关键是看措施是否产生了有效制止和预防明显侵权的效果。被告作为国内头部短视频平台,在权利人多次投诉情况下,依旧有大量的侵权视频传播,说明所采取措施并未实现平台上无明显涉嫌侵权视频的客观效果,难谓合理、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热播影视作品等的主题、内容主动进行选择、编辑、整理、推荐,或者为其设立专门的排行榜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对于《狂飙》这样一部热度极高的影视剧,被诉平台通过设置“狂飙”话题、开辟影视专区等行为,对平台上的侵权视频进行了编辑、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几乎不可能对侵权内容毫不知情。
从“填平损失”看赔偿计算革新
该案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影视剧的侵权损害赔偿额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动辄上亿元的影视制片成本、售价与几十万、几百万元的侵权损害赔偿额形成鲜明对比。2021年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云南虫谷》案中作出了3200万元的判决。有部分观点认为,在行业类似案件普遍判赔几万、十几万元的情况下,法院通过宽泛的酌定赔偿方式,作出高于法定赔偿500万元的上限的判赔金额,将会面临缺乏合理性的质疑。
事实上,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及权利使用费标准为优先,次优路径才是法定赔偿。损害赔偿的目的是填平权利人因侵权遭受的损失,使其恢复到未受侵权的原始状态。因此,当可以通过实际损失、违法所得以及权利使用费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自然无须适用法定赔偿,赔偿数额也当然可以超越法定赔偿额的上限,这也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要求。
《狂飙》案中,法院综合考量案涉作品知名度及商业价值、被告侵权情节及侵权规模、平台规模、性质及获益等因素,已经认定被告短视频公司侵权所获收益超过了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自然不可能再拘束于法定赔偿的限额,适用裁量性赔偿全额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情合理。
而随着著作权作品制作及采买成本的不断提高,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较低的判赔额已经同我国著作权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诉求严重不符。著作权作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单一作品的制作和采买成本上,更体现在热门作品对整个正版应用的支撑之上。经过多年的行业竞争,视频平台在服务、价格方面已经趋于稳定,内容成为平台竞争的胜负手。爆款影视综艺能够直接推动短视频平台付费会员数量增长,并带动腰部内容的销量。特别是影视剧的热播期的市场价值,可以占整个作品全部市场价值的80%以上。
笔者认为,符合影视作品创作现实的高判赔额,才能真正遏制网络侵权行为的泛滥,为长视频内容产业的蓬勃发展筑牢法治保障,让文化传承在数字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光彩,走向世界。
(卢海君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禹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