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唯有高标准 方能动人心
——探秘《何以中国》诞生故事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4-0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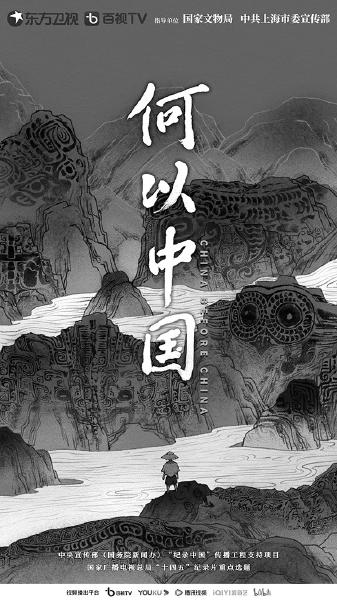

不久前,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获奖名单,《何以中国》获得最佳系列纪录片。奖项公布的当天,《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联系到《何以中国》总导演干超,在表达祝贺的同时,也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这次能多讲点《何以中国》背后的故事吗?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故事来勾勒一部精品纪录片的轮廓。”干超笑称:“那故事可太多了,我想想要从何讲起。”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跟随干超的讲述,我们又回到了《何以中国》拍摄时争分夺秒的时光。
再艰难也要实地拍摄
干超告诉记者,担任《何以中国》的总导演和制作人是一件很有挑战的工作,“因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属于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即复原古代社会”。这一目标意味着庞大的工作量,包括房屋搭建、仪式复原、青铜冶炼、甲骨钻凿等。为此,团队共复原叙事场景220处,做到了“每一幕都有出处”。在横店,《何以中国》摄制组几乎1∶1复原了史前南北方村落,如著名的西坡遗址的部分考古现场等。
然而,到了拍摄时干超发现,美术复原只是一种呈现手段,更佳方案是带着镜头走进历史真实发生的场景和地点,“解忧公主嫁往的乌孙国在今天的新疆伊犁地区,红山文化发源于西辽河地区,石峁的庞大石城屹立于陕西榆林,良渚城则处于天目山环抱的余杭地区……在历史场景的影视拍摄时,我们尽一切可能去这些实景地展开工作”。
为了取得最佳的拍摄效果,《何以中国》影视片段拍摄采用了价值百万元的专业ALEXA 35电影摄像机,拍摄时也按照电影的工业标准进行设置,这要求摄制组在摄制时需要配备灯光和移动轨道等各种器材,因此行动异常困难。干超坦言,他们为此做了一些违背电影拍摄规律的事情,“不论多艰难也要实地拍摄”。如导演组为了给片中的秦始皇寻找一个“雄霸天下”的视角,最终选择在大凉山的悬崖峭壁,这个被誉为“中国最美绝境”的地方进行拍摄。绝境视角自然没话说,但进入的路程异常艰辛。干超告诉记者,团队从下飞机后,开车十几个小时才到达山下,且上山的路也是异常凶险。“我们为这个镜头准备了三个月,前期导演组3次入山实地考察,但实拍的当天正好下雨,滑坡把我们所有人都堵在了路上,现在想想都是心有余悸。”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拍摄三星堆的时候,剧组深入人迹罕至的密林里,吃尽苦头。电影组一些有经验的制片人反复劝说干超放弃,但最终为了效果,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坚持下来。最终摄制组走过全国230余个拍摄点位,资金方面严重超出了预算。为此,整个团队只能在别的方面压缩资金,为期3年的纪实拍摄,导演组成员全程自己开车,拍摄时尽可能提升效率、减少设备使用时间等,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部用于电影化片段的拍摄中。
除了场景和拍摄,《何以中国》在服装上也是大手笔。记者了解到,《何以中国》共制作服装2268套、饰品1500件,按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的说法:“服化道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考古学小论文的题目。”
《何以中国》造型指导王海婷从业至今已有24年,曾参与《神话》《封神榜》等80余部影视作品服饰造型的设计和制作。然而,王海婷发现,依托庞大的考古知识体系,《何以中国》的工作量是影视剧的十几倍不止。在有限的预算下,造型组也是“可着头做帽子”:对于重点人物的造型与道具,不惜成本去打造;对于服装量过大的场景,则是靠造型组“刷脸”去场外求助。干超还记得,有一次要拍摄一个百人行军的场景,群演的服装都是从其他剧组借来的。一件衣服的造价要几万元,且不能出现任何破损与污渍,否则原价赔偿。“本来还想在衣服上增加泥点,以体现行军的艰辛,最后只能作罢。”干超有些无奈地表示。
《何以中国》的解说词既大气又唯美,让不少观众沉醉不已。干超表示,过去纪录片的撰稿通常是一个人从头写到尾,而《何以中国》的文稿大纲由秦岭带领北大编纂组制定,累计有十几人参与,最后由中山大学的周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新伟两位老师定稿,前后总共撰写了五遍,脚本多达40万字,“每一遍都是在颠覆中不断进步,而且每一遍的费用都无法节省”。
由此,《何以中国》的预算一直在缓慢攀升着,但干超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只有在高标准下,作品才能有震撼人心的质感。如果我们得过且过,终会留有遗憾”。
精雕细琢每一处细节
不想留有遗憾,还要在细节上精雕细琢。《何以中国》共制作道具3600余件,可谓件件精品。如为了追求饰品真实质感,团队赶赴安徽,在道具预算已用尽的情况下,干超自掏腰包,请玉匠打造凌家滩遗址里出土的真玉饰品,想通过镜头传达真玉在人物身上的温度;又如姬昌太姒配饰中的玉饰,是根据西周早期大墓出土的玉器,以及周人用玉制度考古研究,使用真玉来复原的玉组佩;再如祭祀典礼中,良渚王和王后全身配饰的玉器,均是根据反山大墓出土玉器复原,由今天良渚地区优秀的玉匠阿玉耗时数月打造,并还原了良渚时期玉质的颜色。干超介绍,现在在博物馆看到的不少良渚玉器呈鸡骨白,这是玉深埋在地下数千年受沁后呈现的颜色。而这种玉质本身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时期是浅绿色的。“之后我们将照片发送给良渚遗址管委会,他们回复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把玉的颜色做对了,值得表扬’。”干超说。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团队复原的两只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鹰道具,被陕西考古博物馆留下做展览;团队复原的商时期的炼炉浇铸系统,被研究殷墟的专家建议用于新的殷墟博物馆展示……“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不用做那么苛刻、细致,但我们觉得做就要做到最好,这是我们对百年考古的尊重,是对中华文明的尊重,我们也相信观众能够体会得到这种温情和热爱。”干超表示。
这种对创作的精雕细琢还体现在表演上。“群演不够、导演来凑”,为了节约成本,《何以中国》执行导演王凯亲自上阵,虽然他在片中多数呈现为剪影或者背影,但他还是买了不少表演专业书籍学习。“他想观察人物,思考如何将剧中人物的内涵气质和真实感传达给观众。”干超解释道。
为了让表演更生动,王凯甚至给群演做起了指导。干超回忆,有一个段落是讲述商九世之乱时期,商朝中衰,部分贵族离开都城。按照一般的表演要求,群演只需要走出凌乱的队形,即可完成这个象征性的场景。然而,到了拍摄现场,王凯却不厌其烦地和群演分析感情细节,他要求群演了解商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纷争的原因,并合理想象具体人物在面对剧变时个体的无措和矛盾心理。
“虽然这些与剧情文本无关,但是他会让群演从现实中走出来,从历史的角度了解自己在面对什么场景。处于一个历史节点,即使是普通人,也会有自己的时间分量。即便这种分量是轻微的,我们也希望表达出来。”干超如是说。
用行动反哺考古行业
《何以中国》有这样一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在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摄制组邀请到了考古学家吴卫红、张小雷,将07M23号墓的300件玉石器从库房里“请了出来”,重新按照5000多年前贵族入葬时的情景,将随葬品进行层层摆放。
这些玉器平时就难得一见,重新摆设更是前所未闻,这让人不禁好奇《何以中国》团队用了什么办法去说服这些考古人员。对此,干超只给出一个答案,那就是“真诚”。
干超坦言,在沟通拍摄时,进展并不总是顺利的。“有一些考古人员认为摄制团队只想把他们当作解说的‘道具’,而不是真正尊重他们在学术上的认知或者研究。但后来他们发现我们是非常认真地开展专业学习,每次见面都能与他们讨论研究成果。他们确定我们要做的是一部真正秉持考古写史精神的纪录片,最终对我们敞开了心扉。”
做研究的人,敞开心扉后情感都是热烈的。在拍摄时,几十家考古工作站、数百家博物馆给予了摄制组最大支持。“比如三星堆博物馆,我们前前后后去了4次,当地馆员每次都非常耐心,甚至陪同我们拍摄到后半夜。”干超介绍,《何以中国》的高标准拍摄,也让各地博物馆无形中提高了后续的拍摄门槛。“一家国家级博物馆的馆长就曾说起,他们现在审核其他摄制组拍摄申请时,要求就是要达到《何以中国》的摄制标准。”
纪录片的成功离不开这些考古学家的辛勤付出和无私指导,而《何以中国》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反哺学界。如片中所使用的地图,80%均为首次创作呈现,由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以及地图编审反复核查、研讨,每幅地图的平均修改次数为32次,使之不但成为视频的一部分,同时也具备了学术价值。“在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考古杂志对地图编审非常严格的环境下,我们最终成功地展示了这些地图,有几张地图已经被考古所或考古学家在发表文章时引用。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干超表示。
此外,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老师向干超反馈,他们在教学中使用了《何以中国》某些复原场景、图片或文物等,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本知识。这种引用不仅提升了《何以中国》的学术影响力,也让更多人了解了团队的研究成果。干超表示:“我们受到了考古学家无私的指导,受惠于他们,现在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哺,共同推进了考古事业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