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的书房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3-0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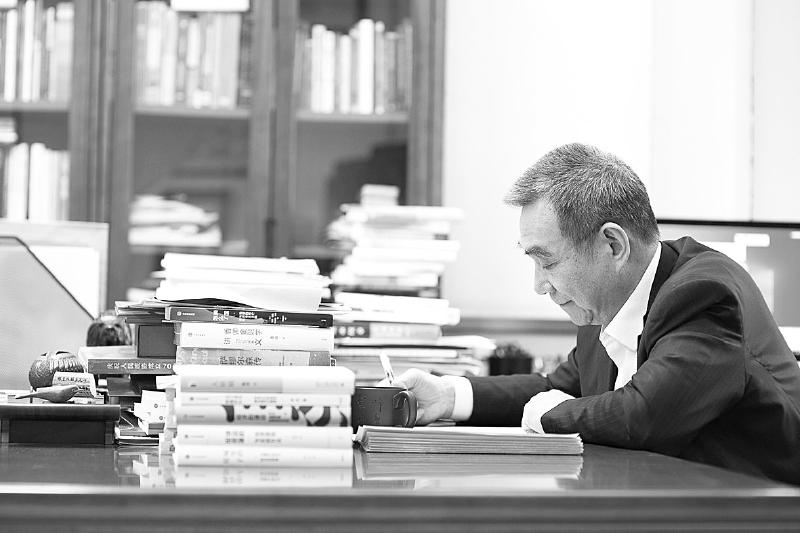
董强的书房
跨越时间与国界
书房,可以投射出一个人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在这个由中文和法语讲述的微缩世界里,远近交融,中西结合;一半现代,一半古典。
书房里,靠墙的实木书柜格间中,书籍被整齐地归类:一半中文书,一半法文书。顶上,一半是大部头,另一半则堆放着有些年岁的录影带,褪色的包装,给整面书柜平添了几分岁月的厚重感。
书柜前的空间是董强的活动范围,一半现代,一半古典。北面是办公桌、电脑、打印机和一堆书籍,简约清爽,这里是他进行法语翻译和教学准备的工作区;南面则是书法台、毛笔、砚台、宣纸、印章……散而不乱地铺放在台面上,董强擅长书法,工作之余总是要写上两笔。
董强喜欢在书柜前放置一些小物件。每前往一个国家,遇到特别能够体现当地文明的物件,董强都会买下一件。久而久之,世界各地的元素浓缩于此,勾勒出一个中国文人行走、体验、感悟的世界模样。物件的类型很丰富,琳琅满目。
书房里挂着或摆放着董强喜欢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法国待过的艺术家,我给他们写序。”王衍成、江大海、瞿倩梅、范一夫、王刚、陈江洪……“书与艺术是最搭的”。
“书房其实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想象的世界。”董强解释道,“这里的只是一小部分,我总共的藏书没计算过,但真的不少。”
最让董强感到震撼的书房,是他在法国求学时的导师米兰·昆德拉的书房。“他有一片巨大的书柜。我很好奇,结果发现里面全是他自己写的书!被译成了全世界的各种语言!”由于藏书颇多,他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可以流动的书房,不仅书房本身可以像蜗牛的壳一样跟随着人一起移动,里面的书目也可以及时更新。
随处随时都能专注阅读
从邻居家到北大图书馆,从朋友家到法国书店,书中之思想成就了董强,而他也挑出珍贵之物赠予学院图书馆。借书以读之经历亦练就其专注力,为日后做学问夯实基础。
虽然自己的藏书不少,但董强却别有心得:“书非借不能读也”。
董强从小学起就爱读书。小时候家里没什么书,他就经常看姐姐的教材。藏书较多的邻居家,也成了董强儿时的图书馆。
20世纪80年代,16岁的董强进入北京大学,被分配到西语系修习法语,从此开始了与法语毕生之缘分。图书馆是他在校期间最常去的地方,其中法语藏书为他提供了学习的第一份养料。但书籍资源终归有限,青年董强十分羡慕法国朋友家中丰富的藏书,每每拜访,都有想要全部复印下来的冲动。
本科结束后,他以全国统考第一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赴法深造。此时的董强,对法语乃至法国文化均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法国,董强大量的时间都在书店度过,经常读到店面打烊。因为不好意思只看不买,他就每次挑一本不太贵的买,逐渐积攒了不少书。后来回国,在法国留学时所购之书,董强一本不落地全数带回,还挑了一些比较珍贵的,捐给学院的图书馆。
由于总是“借”书读,和很多爱书之人不一样,董强对书籍并没有强烈的拥有感,“书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思想,并非实物本身”。此外,他还练就了随处随时都能读书的本事,无论嘈杂与否,拿起一本书就能快速沉浸其中,专注阅读。
“专注力是读书人的重要品质。”董强说,“不光是读书,做学问也是,要专注。”他也常勉励学生,看一篇文章就要完整地看完,要保持内在的安静,不能因为任何事分心。
林毅夫的书房
于胸中丘壑处漫步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看来,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是胸中丘壑,是所见万物。
推开门,一整面墙的木质书架映入眼帘,没有任何点缀的棕红色书柜同园外的风景一般,庄严又古老,成百上千本书籍整齐地排列着。从《唐诗三百首》等古籍经典,到《农村全面小康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等现代策论,小小的书架凝聚着博古通今的力量。
在介绍自己的书房时,林毅夫却只淡淡地说道:“我的书房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一排书;家里也有办公室,也有书。”
在他看来,真正的书房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是一种心境、一种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大块假我以文章”,真正的书房并不局限于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飞机上,在火车里;甚至在开会,在听报告,在调查研究中。但心里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对现象、对社会的好奇,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
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源自朋友,可能是城市的一角,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如孔子所说,“吾不如老圃”,身边的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他们的认知,就构成了书房。
在林毅夫的认识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关心,每一种现象都应该被思考。他说:“如果把对社会、对时代的关注也视作读书,那是无时无刻不在阅读的。”
珍藏最根本的智慧
在身边、在脑海里,他始终与经典之书相伴,亦常读常新。他不排斥阅读载体随时代更迭变化,而是坚持着“打破砂锅问到底”,汲取书中最根本的智慧。
“有几本书是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搬几次家,都会珍藏下来的。那样的书不多,但可能就是最根本的。”年幼时期的林毅夫对书籍涉猎广泛,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每一种对世界的理解都被他输入脑海。后来读了大学,进了研究所,他读的书逐渐趋向专业化。虽已阅读无数,但在林毅夫看来,“书重要的不是买了多少,而是留下了多少”。
有些书丢了,有些书因为搬家被留在了原地,但总有几本书会一直留下来,留在身边、留在脑海里,那些书被看了两遍三遍,有了新的心得体会都会写在上面。
在他眼中,那是一些经典的书,比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老子的《道德经》、六祖慧能的《坛经》以及《金刚经》等,它们是几千年来留下的智慧,传道授业解惑之“道”,无论哪行哪业都在读的经典。“如果将来什么书都可以舍弃,那几本发黄的书我也会留下来,珍藏下来。”
谈到对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选择时,林毅夫认为,处在不同的时代,总是要选择相应的最有帮助的载体。过去没有电子书,只有纸质书,一些古籍经典甚至连索引都没有,查资料要靠博闻强识。现在不一样了,大部分知识信息都可以电子化,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唯有了解各种知识背后的道理,才能灵活运用,他反复提到:“任何知识都是刻舟求剑,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一定对。”
(本文选自《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