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介入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3-0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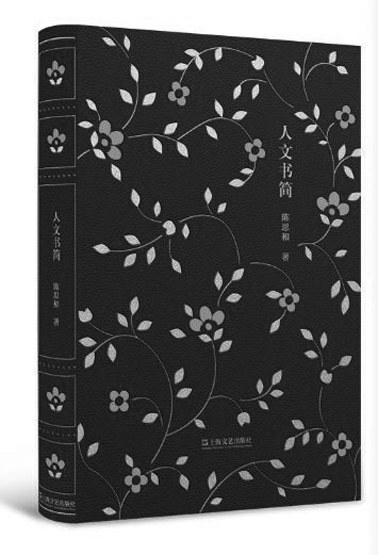
一般来说,书简文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通信,不准备发表给公众看的(至于以后让他人发掘出来公开发表,又当别论);还有一类借助书信体形式做文章,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但后一类书信还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借助书信形式来进行另一种文体的写作,如用书信体写文学批评、写散文,甚至通过书信来探讨深奥的理论问题。在我早先的阅读经验里,最早接触的这类体裁的作品,是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这是讨论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经典之作,还有就是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书简》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作人有一些当作散文小品写的书信,也属此类。当然,书简可以构成虚构作品,如书信体小说,但这已经超出了书信自身的界定,不属于我这里所说的范围。我所指的“书信”,首先就是书信——借助书信形式来讨论理论问题或者批评某些作品,都还是书信所包含的功能之一,所以这些文章确实是书信。
这本小书收录的书信体文章,不属于私人通信,大部分都是公开发表过的。其中有一部分还收入了我的编年体文集。之所以要编这样一本小书,纯粹出于好玩。起因是这样一个故事:我的朋友张安庆先生想为学者策划一套“边角料书系”——不是学术论文集,更不是高头讲章,而是学问中的“边角料”,也是形式上比较活泼自由的学术研究副产品。他来向我约稿,我自然要支持他,于是答应先编两种“边角料”:演讲集、访谈集。在编辑过程中,又渐渐想到了可以再编一本书信集,这个念头一旦有了,就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说起来时间就长了。从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写评论,即尝试着用书信形式。那时我还在念大学,在《上海文学》发表第一篇评论,是评论陆星儿、陈可雄的中篇小说《我的心也像大海》,我用的是书信体,虚拟了一个读信对象。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写法?我现在也想不太清楚,不过深究起来,大约是因为小说的作者之一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但读认识的人的作品,还是有一点亲切感。所以准备写评论的时候,眼前就似乎一直有个具体的“人”存在,他就是我的写作对象。他或者是小说作者本人,或者是读者,因为共同阅读这篇小说,就变得彼此熟悉起来,似乎有了对话的欲望。这种感觉,不大可能出现在阅读一个陌生作者的作品过程中。而且,这里还不仅仅涉及一种文体的选择,我觉得更多的是批评者立场的选择。文学批评,无论如何总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但用书信体则可以避免这种令人尴尬的关系,使批评成为一种对话,无论对作品赞扬还是批评,都是处于平等的对话的立场。这样,写批评的心情就轻松下来了。
学习写作,选择什么样的起步方式,往往对自己一生的写作都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从学习写文学评论开始,就主动采用了书信的形式——后来又主动尝试过用对话的形式、序跋的形式、随笔的形式,总之是想尽可能地摆脱学术论文模式,尽可能言之有物,面对作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这样一条自我设定的学习道路上,书信形式渐渐成为我得心应手的表述形式。本书第二辑“与文学评论有关的书简选”和第四辑“避疫期间的书简选”主要选自这一类文章。
除了这一种以书信体来承载文学批评(或其他文体)功能的形式外,还有一种公开发表的书信形式的文体,主要用于互相交流和传递信息。书信还是书信,但由于传递的信息含有某种特殊意义,它的公开发表就使文本超出了书信的一般意义。我这次特意挑选其中一部分信件收入本书,还特意加了两封当初没有公开发表的书信,为的是让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呈现得更加清晰一些。
《人文书简》
陈思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