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早期中国社会图景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3-0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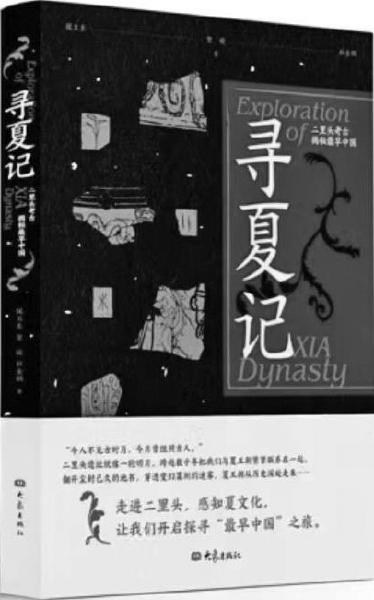
想探寻夏朝真正崛起的线索,需要从二里头文化说起。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流域以及更南方的地区相继发现了越来越多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文化遗存。这表明,至少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国大地上的诸多邦国终于出现了“统一”的迹象,这也意味着上古时期的中国社会渐渐地从那个群雄并起的“邦国时代”走出,步入了“王朝时代”,散落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先民们,最终站在了同一个图腾之下。
最近出版的《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大象出版社)就记录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诸多细节与故事,不仅复盘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历程,还颇为详细地介绍了二里头遗址所展现出的先民们的生活、工商业以及对外交流。依托扎实的资料和研究,向世人揭示了3000多年前那个伟大王朝的一角,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翔实的最早中国的社会图景。
在《寻夏记》的开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首先为我们论述了探索夏朝文化的理由。中国的考古学背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它需要去回答中华民族、华夏文明从何而来又如何发展的问题。不论哪朝哪代,中国人始终都在追求统一——那么,对夏朝文明的探索也就成了必须去完成的一项任务,因为它承载了最早中国的历史记忆。
《寻夏记》梳理了百年学案,让我们看到了数代考古学人的艰辛探索和孜孜以求,也让我们了解到,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使二里头文化全为或主体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认识,渐成共识。
除了陈述探索夏朝的重要意义,《寻夏记》还为我们完整呈现了夏朝的时代风貌。
以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为例,它大致位于二里头遗址的中央,扼守了整个二里头遗址的核心位置。按照杜金鹏研究员的观点,“这是中国古代王都‘择中立宫’的最早实例,十分真实地体现了当时尚中、贵中的思想”。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呈现出了明显的“东西对称”——它有一条明确的中轴线,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南北排列,组成了都城的中轴线。这种城市规划思维,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二里头遗址也成为了目前已知中国最大的按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里头遗址墓葬中,人们发现中国古代的“龙崇拜”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二里头遗址之前,辽宁阜新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就发现了用红褐色玄武岩石块堆砌的龙形堆石,在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墓葬也发现了用蚌壳堆砌的龙,在湖北黄冈焦墩遗址则发现了用卵石摆塑的龙图形。到了二里头遗址中,“龙崇拜”进一步强化了,开始出现了立体雕塑的龙和平面刻画的龙,还发现了用绿松石片组合成的龙。
而“世俗生活面面观”一节中,《寻夏记》为我们展示了夏朝世俗生活的诸多侧面。二里头遗址中的发现表明,二里头时期,“五谷”已经全部出现,农牧业发展痕迹很明显,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粟、黍、水稻、大豆、小麦。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榛子、板栗、菱角等果实类食物以及猪、牛、羊等家畜。
除了农牧业,各种类型的手工业在二里头遗址中也有体现,这些手工业门类包括:青铜冶铸、玉器制造、漆器制造、陶器制造、骨器制造、石器制造、竹木器制造、纺织业。相应地,也发现了各种容器、武器、工具甚至出现了乐器、礼器等等文化性器物。二里头遗址中的手工业部门不仅门类繁多,规模也颇为壮观。其中,仅仅是铸铜作坊就达到了1.5万—2万平方米,其中还可以分辨出不同的车间。凡此种种对二里头遗址细节的描述,书中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言。
总而言之,作为一本面向全社会的大众读物,《寻夏记》并不像一些考古学专著那样晦涩难懂,而是采用了一种朴实的语调为读者展开了二里头遗址昔日的光彩和辉煌,是一本了解二里头遗址、了解夏朝社会文化的优秀读物。该书对最早中国及中华文明根脉问题的解读,将架起一座学界与大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