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书事余墨》中的编辑哲学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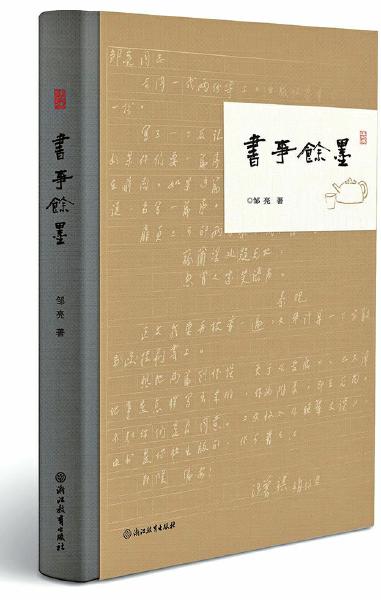
一位印刷厂的资深总监看到我近期正在读邹亮先生的新作《书事余墨》(浙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3月版),与我说起,他30多年前上大学时如饥似渴地读过大量先锋文学作品,并且至今仍记得这些作品都出自同一位编辑之手,他就是——邹亮。这位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走出来的著名“文学操盘手”,30多年来打造出一本又一本的文学经典,为浙江的文学出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借着《书事余墨》这本书,我们可以一窥作者的编辑哲学。
编辑的双重身份:文学守护者与时代记录者
一直以来,本书作者将自己定位为文学参与者,去见证、总结当代的文学发展。在《书事余墨》的代序中,他用细腻的笔触回溯了那个“文化寻根”勃兴的年代,让我们看到编辑与作家之间珍贵的交往点滴,那些与作家彻夜谈论文学的场景令人难忘。作者有着敏锐的文学触觉,鉴于当时新的文体实验兴起,他力主扩大浙江文艺出版社“系列小说书系”规模,陆续推出了汪曾祺的《菰蒲深处》以及叶兆言初试啼声之作《夜泊秦淮》,还发掘了苏童早期的女性题材作品,这些在当时看来有点超前的文本,如今早已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后来书系规模日丰,梁晓声的《黑纽扣》、贾平凹的《逛山》、王安忆的《三恋》、马原的《游神》、格非的《青黄》等相继出版,成为一时佳话。
本书作者笔耕不辍,常鼓励年轻编辑,不仅要“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还要勤动笔头、多写文章。书中第一辑“书里书外”收录了他过往颇具代表性的书评。他对《都市风流》的结构分析、对《闯荡都市》中城乡冲突的解读,都体现了专业编辑的文学洞察力。这些文章不仅是对作品的深入解读,更是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捕捉。当他在《环境与人的双重污染》中探讨《涨潮时分》的生态主题时,实际上是在书写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当他在《讲述走向世界的温州精神》中解读《巴黎有片榕树林》的家国情怀时,实际上是在书写以浙商为代表的出海浪潮;当他在《以稀土书写中国人的强国梦》中剖析《淬炼》的意象表达时,实际上是在书写面对“卡脖子”难题时我国科学家的使命担当。
编辑的价值认同: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突围
本书作者的编辑哲学始终贯穿着对文学本体的坚守。在《文学出版: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求生存》一文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商业化浪潮下的文学出版面临着严峻挑战,但真正的编辑应守护文化理想。他引用美国大学出版社的领军人物达塔斯·史密斯的话,认为编辑出版者应具备“政治家的高度文化素养和商人的远见卓识”,这种双重定位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编辑在市场运作与文化传承间的平衡艺术。这种理念在他策划的“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中得到充分体现。该丛书首次系统梳理了“新写实”“新历史”“新乡土”“新笔记”“新都市”“新实验”等文学思潮,为当代文学建立起清晰的谱系。
全书流淌着作者对文字的敬畏之情。他提到编辑《中国院士》时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为核实某些重大科技成就涉及的院士准确名单,他多次向中国科学院发传真核实,要知道那时连电话通信都尚未全面普及,足见编辑工作之烦琐艰巨;为提升书稿的思想内涵、艺术质量,他与作者反复推敲每一处细节,前后还举办了3场书稿讨论会,书稿字数从55万字精简为35万字。这种对文本苛刻的要求和虔诚的态度,使他赢得了众多知名作者的信任。在《散文是高难度的写作》一文中,他强调写散文要“文史哲打通”,这种观点也同样被他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中,让作者开启跨界创作也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浙江文艺社的“学者散文”系列的推出,正是这种理念付诸实践的例证。从杨绛的简练克制到费孝通的深刻洞察,从钱钟书的隽思妙语到施蛰存的诗性语言,这些作品展现出文字特有的魅力。
编辑的精神图谱:在文字长河中寻找永恒
正如作者在《兰登书屋前留影》中表达的:“贝内特·塞尔夫和那个时代的兰登书屋,出版人生命中的美妙精彩莫过于此。”这种对出版事业的热爱,使他的文字充满温度。《书事余墨》中那些关于选题策划的细节、与作者往来的书信、审稿时的灵光闪现,甚至是对重要奖项的总结和思考,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编辑精神图谱。
其实,书中最精彩的篇章藏在第三辑“读书生涯”里。例如,他在《略论现代派文艺与儿童文艺的契合及其原因》中,突破了传统儿童文学理论框架,将儿童文艺创作提升到人类艺术本源的高度。当他分析蒋风的儿童文学观时,也开始思考文学教育的本质,即如何在童真与社会规训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些扎实的理论叙述,加上诗意的文字表达,既展现出其清晰的思考洞见,也表露出其不断探索的精神追求,更可以从中窥见邹亮先生作为学者型编辑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字时代的冲击下,作者始终对出版业的未来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他在《元宇宙与出版业的前景》中提到,没有内容支撑的科技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科技加持的内容是没有未来的。的确,技术的革新不应消解内容的价值,反而应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可以说,这种前瞻性思考,使《书事余墨》超越了一般个人文集的范畴,增添了行业启示的意义。
一部文学史,是一部作家的创作史,也是一部编辑的奋斗史。当我们谈论一本书时,不光是书中的内容,书背后的故事同样值得我们回味。“书比人长寿”,留传下来的好书,本身就留有编辑的人生印迹,也是编辑事业的嘉许状。
(作者系浙江教育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