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参与翻译首版《拉贝日记》算起,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这本书也有了多种版本,“从青丝干到白头”的刘海宁说:
与拉贝结缘是没有终点的工程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8-11

《拉贝日记——敌机飞临南京》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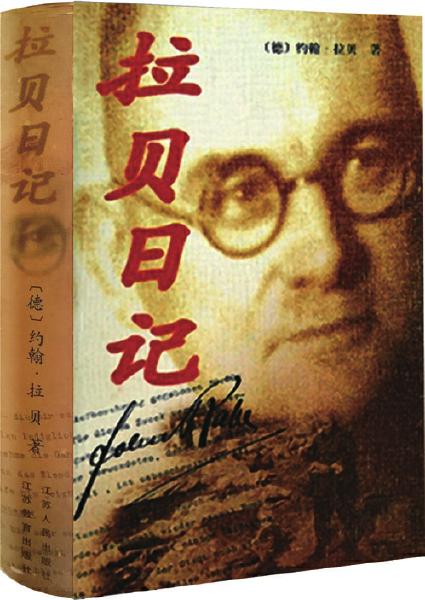
《拉贝日记》国际首版(1997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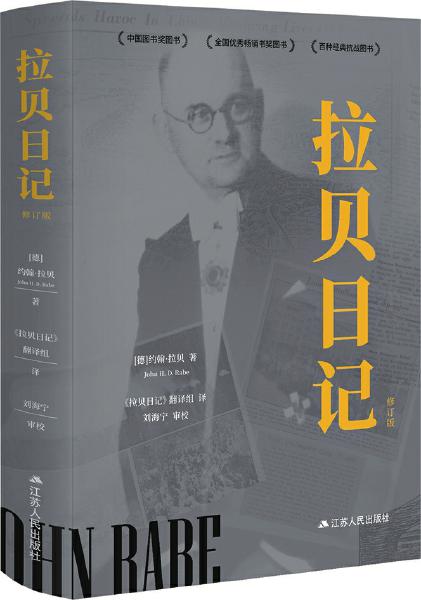
《拉贝日记》(修订版)(2025年8月出版)

2017年12月,《拉贝日记》(影印本)发布会现场,刘海宁(右一)等译者与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夫妇合影。 江苏人民出版社 供图
“我要亲眼看看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对这种残酷的暴行是不能沉默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拉贝的“战时日记”,一天不落。
南京大屠杀现在能以真实的全貌逐渐展现在后人的眼前,离不开约翰·拉贝和他的《拉贝日记》。1997年,中文版《拉贝日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为世界首版。从1997年至今,该书所有版本的发行量已难以确切统计,仅近5年销售量就超过10万册。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拉贝日记》(修订版)又刚刚上市。
自1997年参与翻译首版《拉贝日记》算起,“从青丝干到白头”的刘海宁与拉贝“相识”近30年,“通过参与《拉贝日记》的翻译,我从对拉贝一无所知,到渐渐熟悉拉贝,进而发展到现在对拉贝产生了深深的感情。”8月6日,刘海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翻译《拉贝日记》是我从事各类翻译中,持续时间最长、介入最深、考证最多、责任最重大的一项任务,感觉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结束,永远都是进行时。”
“赶工”国际首版:翻译组和编辑“关在一起”
1997年5月,正在南京大学德语系工作的刘海宁接到江苏人民出版社邀约,与来自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6位老师,组成了《拉贝日记》翻译组,“那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日,这本书要在那之前出版。”那一年,刘海宁37岁。
“翻译《拉贝日记》,是我第一次在对一本书的作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动笔的。那个时候有关拉贝的资料很少,没有什么可供查阅的资料。”刘海宁追忆道,自己以前翻译图书都是“单打独斗”,“因为这本书,头一回参加如此多人的‘团队作战’。”
“为了便于大家之间的协调和统稿,我们全部集中在南京高楼门宾馆夜以继日地‘赶工’,仅用一个半月,就完成了约50万字的翻译任务。”刘海宁回忆说,当时来自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精通德语的编辑蔡玉华和包建明,以及来自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编辑章俊弟同翻译组成员“关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
“还历史以真实”是历史类图书的翻译底线,也是《拉贝日记》翻译组一以贯之的原则。而“准确反映《拉贝日记》的原貌,为世人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和拉贝其人提供真实可信的史料”则是当时出版工作者坚持的信念。“我们意识到,编好这部书稿,首先要有科学的理性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首版《拉贝日记》的编辑手记中写道。
在最后的校译统稿阶段,包建明经常到刘海宁家与其沟通交流。“我俩碰在一起琢磨每一段可能有歧义的原文,推敲每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翻译,力争做到表述和原文正确无误。”刘海宁回忆说。
1997年8月,《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面世,迅即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自此,刘海宁与拉贝及《拉贝日记》结缘,开启了自己翻译生涯中这项看似没有终点的工程。
编译良性互动:推动日记常出常新走向世界
从1997年首版至今,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拉贝日记》相关图书,包括单行本、影印本、青少版、全译本以及修订版等。“这既是一种出版使命,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历史和国家赋予的责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保顶说。
刘海宁参与了所有版本的翻译工作,他也成为《拉贝日记》多版本开发的审校者及译者联络人。
《拉贝日记——敌机飞临南京》是拉贝日记最原始的版本,书名也是拉贝自己命名的。刘海宁当时负责统筹翻译6卷8册的原件,他回忆道:“拿到手时,文件很多都是无序的。因为是日记体形式,所以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逐步理顺、厘清文件原件,为读者呈现出拉贝日记的原貌。”
《拉贝日记》责任编辑汪意云介绍,目前只有中国独家拥有《拉贝日记》的版权,“我们计划把它翻译成各种文字推向世界。”
“现在新一任编辑曾偲接手《拉贝日记》,她以全新的思路,从深度和广度去挖掘《拉贝日记》的内涵,让日记以全新的形式更加符合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出版日记的青少版便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刘海宁说,抗战历史完全可以以合适的方式成为青少年读物,“让他们知道,在80多年前,南京都发生了些什么,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进而促使他们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这类悲剧在人类历史上重演。”
刘海宁特意为《拉贝日记》(青少版)写了前言和后记。“当时曾偲约我写导读前言,我一直没有落笔,不知该从何开始,始终有一种越了解就越无从下笔的感觉。”刘海宁告诉记者,现在的后记就是最初版的导读前言,“一次我在书店参加活动时分享了自己眼中的拉贝,曾偲听完说非常好,依据这篇底稿,修改成了大家如今看到的青少版前言《拉贝是谁?》。”
“正是编者和译者的这种良性互动,促使《拉贝日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刘海宁感触颇深。
从译者到考证者:他走遍日记中提到的区域
翻看《拉贝日记》,其中涉及众多的人名、地名、机构名和事件名。而这些名称翻译的精准度,会直接影响到后人对历史把握的准确度。
“我们常说,翻译要‘信达雅’。”在刘海宁看来,《拉贝日记》翻译的难点表现在“信”上,不仅仅是译文要准确,不能偏离或者遗漏原文,更多的是要去考证,“就像破译密码似的,将书中提到的人名、地名、机构名和事件名等一一对应上,把拉贝要表达的内容和对象准确地再现出来。”
事实上,当《拉贝日记》首版出来后,刘海宁对《拉贝日记》的工作重点就已经不再是从翻译角度出发对原文的文字进行推敲,而是变成了考证,“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由译者变成了考证者。”
考证的过程,本身就是求索的过程。为了确保后续修订中翻译的地名和地理方位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刘海宁购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一个年份的南京地图,还走遍日记中提到的区域。
“我与刘老师的对话往来基本在‘提问’‘讨论’‘答疑’中转换,经常因为一两个词汇的确认而欢呼。”曾偲感慨道,“2017年初,我作为新一任编辑与翻译组的译者老师们相聚时,所有人都对当时的翻译经历记忆犹新,也为参与了这样一项翻译工作感到自豪。”
“现在,每当我行走在南京街头,看见拉贝在日记中提到过的街道、建筑,与之相关的事件和人物便会出现在我的思绪中,感觉似乎又看到了拉贝的身影。”刘海宁饱含深情地说,“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认为他有爱心、幽默、有胆识、有勇气、有正义感,同时也富有责任感,我对他的认识随着考证的推进不断丰富且丰满。”
现在已经65岁的刘海宁马上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拉贝日记》的考证修订中,“和历史相关的书,你永远不可能说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我们只是尽可能地为读者还原历史真相。要让读者铭记,约翰·拉贝,一个中国抗日战争史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字;《拉贝日记》,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永远都会提到的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