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礼法丛书:十年一剑的法律文化成果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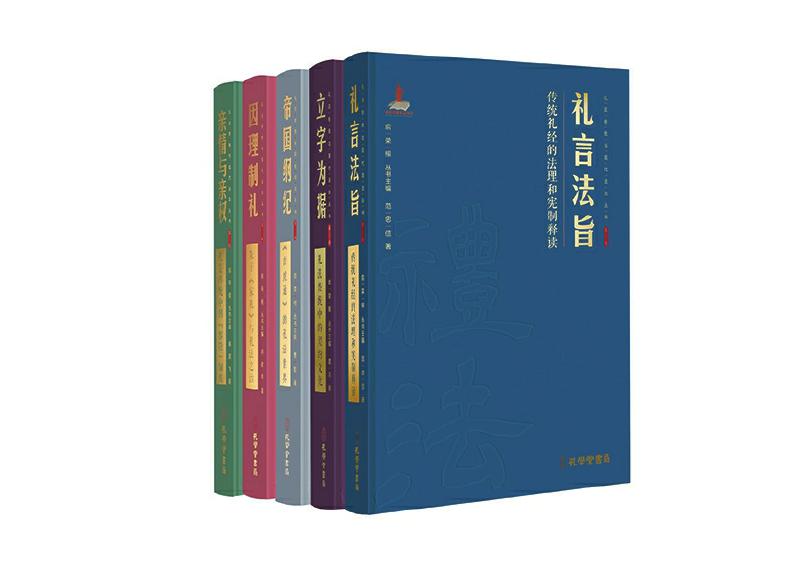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经萨义德《东方学》扉页的引用而广为人知。随着西方法律文明的介入,中国传统法制“被表述”的历程也就开始了。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进程,从而也就不仅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对“被表述”时使用的概念工具保持审慎的反思,努力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提炼自己的概念工具,尝试中国法律史的自我表述,这是重新理解中国法治的前提。俞荣根教授主持的“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以皇皇3辑14册的规模,向我们昭示了这一努力与尝试的成果:中国古代法不局限于律令,而应当表述以“礼法”。我有幸得到孔学堂书局赠书,尤其看到刚刚出版的第三辑5册新作,体会到“礼法”之论的几点微意,将初步的阅读体会笔之于书,向俞先生及丛书作者们致贺并请教。
首先,“礼法”不是“礼”与“法”的简单叠加。
以“礼法”把握中国古代法,不是新鲜事。但学界所谓“礼法”往往是“礼”与“法”的叠加。俞先生在丛书总序中特别强调:“此‘礼法’不是‘礼’与‘法’的合称,也不是‘礼法合一’‘礼法融合’的意思”,而“是一个双音节的法律词汇,一个双音节的法哲学范畴”。这番话在丛书第一辑第一册《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俞荣根、秦涛合著)又有更深入的申论。古人云:“辞之重,句之复,其中必有美者焉。”作者再三强调“礼法”不是“礼”“法”两个要素的合成词,其中有很深的微意。“礼”与“法”合并的“礼法”,容易让人联想到“外儒内法”“明刑弼教”“以儒术缘饰律令”一类的帝王统治术,是一种说一套(礼)做一套(法)的相当虚伪的统治策略。但俞先生及其团队揭示的“礼法”,是以礼为合法性衡量标准的治国规范的总和。此种意义上的“礼法”论对“礼+法”“礼与法”之说构成了严肃而深刻的反思。
其次,“礼法”是有理想的法。吕思勉《中国通史》的“刑法”篇云:“个人在社会之中,必有其所当守的规则。此等规则,自人人如此言之,则曰俗。自一个人必须如此言之,则曰礼。”礼起源于习俗,所不同者,俗是实然的、自发的,民众日用而不知;礼则是应然的、自觉的,经过了人类精英(即所谓“圣人”)的理性审视、精心提炼。《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说,礼法“是中国古代文化之‘道统’在法制上的体现……承载了志士仁人追求‘良法善治’的美好设计与愿景”,就是在此意义上立说的。这与陈寅恪所云“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Eidos者”,其实都是一种对传统法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异曲同工的努力。泛观丛书中的宋大琦《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徐燕斌《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范忠信《礼言法旨:传统礼经的法理和宪制释读》、刘依平《因理制礼:朱子〈家礼〉与礼法之治》均从各个角度发掘了礼法的理想法面相。正是这一重面相,揭示“礼法”乃是中国古代的“高级法”,优于强调工具性的律令法,即便君主也要受到相当的制约。
再次,“礼法”是有古老历史渊源的法。
纯粹出于理想的法,容易为统治者利用,以理想之名给民众的现实生活带来灾难。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礼法”为何能避免此种后果呢?因为“礼法”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生活根基。从时间上讲,礼法是一种“百王之所同”的先王之法,早于秦汉以降任何一个现实政权。礼法以经典的形式白纸黑字地写定,历代君主最多只能以注释的形式利用,而不可能直接篡改。儒家士大夫是礼法的忠实守护者、坚定践行者,他们构成了古代四民社会之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决定了君主不可能在礼法面前为所欲为。曹勤《帝国纲纪:〈白虎通〉的礼法世界》以具体个案,研究“先王之法”如何被现实政权确立为“国宪”;陈坤《天子门生:礼法传统中的科举取士制度》讨论“士”阶层如何被政权吸纳,又如何以礼法影响现实政治、司法;秦涛《天理·国法·人情:礼法传统中的狱讼制度》则陈述在以上种种配套制度包围之中,律令体系的狱讼制度是如何良性运作的;陈鹏飞《亲情与亲权:礼法传统中的“容隐”制度》,通过在礼法体制视野下重新识读“容隐”制度,揭示礼法对刑律中公权力的制约,及其对户本位下亲权的维护。反观律令,是君主建国之后的立法成果,可以根据君主意志立废修改,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在礼法统摄下的律令,才真正具有合法性、延续性。所谓“非礼无法”,不符合礼法精神的法律,即便是君主金口玉言,在合法性上也要打个折扣。
最后,“礼法”是有深厚生活根基的法。
如前所述,“礼”是从“俗”中提炼而来,民众日用常行的生活习俗就是“礼法”的源头活水,保证了“礼法”的强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不需要聒噪不休的普法,因为礼法是从民众从小耳濡目染、社会熏陶而来;不需要大规模的暴力执法,因为礼法往往通过社会制裁作用于人的羞耻心来实现;不需要事事闹到官府、动用国家机器,因为有宗族长辈、乡里父老等社会权威便有资格解决大多数民间“细故”。高其才《礼失野求:礼法的民间样态与传承》从总体上研究礼法的民间样态与传承,陈寒非《讨个说法:礼法传统中的“细故”纠纷解决机制》从运作实态讨论礼法传统中的“细故”纠纷解决机制,丁新正《合二姓之好:礼法传统中的婚姻制度》、邓长春《光宗耀祖:礼法传统中的继承制度》、瞿见《立字为据:礼法传统中的契约文化》则分别探讨礼法制度下的婚姻、继承、契约制度。以“礼法”的目光下沉,“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的争议可以在人间烟火气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左传·昭公元年》云:“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一个古老的国家能够长久存续于天地之间,必有其独特的立国之基。“礼法”之论正是从制度层面,对此种立国之基进行“自我表述”的初步尝试。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的礼法也有其不可忽略的负面价值。尤其在宋元以后,道学、礼教、科举均出现了僵化、形式化的趋势,君主驾驭专制政体的技艺日趋娴熟,破坏礼法的阻力也越来越小。这些现象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丛书对此已有揭示,仍可深究,希望未来能够进行专门的研究。
最后必须指出,“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是出版社与高校学者团队精诚合作的一个典范。孔学堂书局从2015年策划本丛书起,至今年出齐全3辑,十年磨一剑的长期主义在当今学界尤显难能可贵。据说,地处贵阳的孔学堂书局是一家年轻的出版社,“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启动于书局初创之时,10年之中,社长、总编辑等领导层亦曾更换,但对这套丛书却紧抓不放。重识中华法系之礼法传统,以有鉴于现代法治建设,是著、编双方的初衷。书局对丛书的坚守,既是一种“求诸己”的君子之道,也是一种率先“律己”的自觉的契约精神,它是现代法治的入门之卷。
该套丛书的出版,对弘扬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不无禆益的。
俞荣根先生在丛书序文的最后,深情地写道:“‘礼法文化是一座宝库,我们正在开启它!因此,我们对这套丛书充满期待!’对这套丛书,总编期待!书局期待!作者期待!更值得作者和编者共同期待的是,愿她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并得到读者‘上帝’的回音,尤其是批评和指教性的回音。”
随着“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的出版发行,作者和出版者的期待将迎来收获期。作为一名读者,我同样期待这则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礼法之论在学界的回应、争鸣、质疑中更趋完善,更期待中国传统法治文明能有更加精彩多样的自我表达!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