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亦真亦侠亦温文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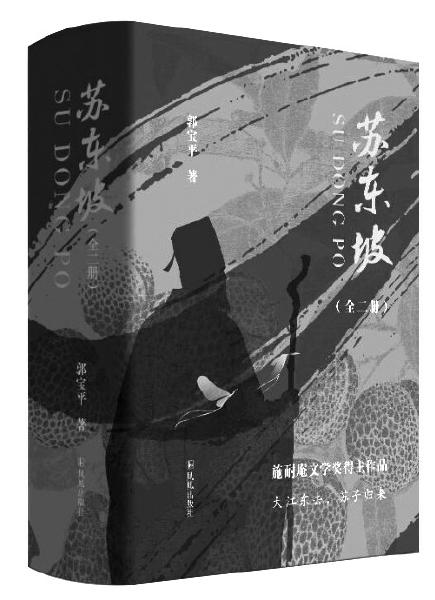
自林语堂以来,现当代中外作家、学者笔下关于苏东坡的生平传记、学术论著、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在当今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在亿万读者和青少年人群中,借助纸质出版与阅读,叠加移动互联网及网剧、短视频等传播介质与传播手段,在城市与乡村、线上与线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东坡文化热”。
在这股热潮之中,作家郭宝平于今年6月推出近54万字、上下两卷本的历史小说《苏东坡》(凤凰出版社)。说实话,打开此书之前,还是为作者捏一把汗的。在诸多宗师大家的名篇巨制之后,从故纸堆中还能翻出多少新意?
带着疑问读此书,连读两遍之后,不仅把心放回了肚子里,还真的可以说,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苏东坡”。一言以蔽之,可用7个字来概括:亦真亦侠亦温文。
亦真:在史料与虚构的经纬中重塑血肉灵魂
以人性审视人物,剖析人物的内心,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血肉丰满、灵魂充盈的生命个体——这是阅读此书后的第一印象。
郭宝平在《苏东坡》中,借助对历史场景、事件、人物和细节的严谨考据与勾连,结合对史料留白处的合理想象和逻辑推理,以深刻的心理洞察和细腻的文学叙事,重新复原了一位个性鲜明、浑身充满着矛盾与纠结、并不完美,然而生动鲜活、复杂立体的主人公苏东坡。
何为“东坡”、何以“东坡”?那个英姿勃发的少年天才,是如何从一心“致君尧舜上”的苏轼,蜕变为了只求“江海寄余生”的苏东坡?时代环境、家风家教、人物性格等诸多内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少年苏轼的成长:从眉山出发,到东京汴梁,进士及第、制科高中;从任职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到乌台诗案,先后贬谪黄州、惠州、儋州,脱下士大夫长衫的苏学士由外而内变身为了躬耕陇亩的东坡居士;最后,遇赦北归路上,“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的东坡先生,老病缠身,客死于常州。他一生奔波劳碌,大起大落,悲喜交加,艰难困苦,曲折坎坷。
郭宝平追根溯源,把苏东坡终其一生都不曾改变的赤子之心和烂漫天真的性格本色,归结于其眉山家风和时代风气的双重滋养。生在家道殷实的耕读之家,祖父苏序的乐善好施、敢作敢为,父亲苏洵的快意恩仇与浪子回头、发奋苦读,母亲程夫人的坚忍担当、慈悲正直与言传身教……如此这般的家风家教熏陶之下,少年苏轼真诚、率直的性格底色得以涵养;而北宋开国以来推崇文治、奖励读书求仕以及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土壤,更让这位天分高而勉于学的读书种子,可以恣意地自由生长。
然而,走出眉山后的苏轼就没那么幸运了。每一次命运的转折,都伴随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与挣扎,他会在暗夜里默念“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也会在风雨中吟唱“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宝平的笔,生动书写了苏东坡斑斓宏阔的内心世界,所有平凡普通人都会拥有的恐惧、落寞、孤独、幽怨、怀疑、犹豫、执着,连同他的坦荡、旷达、豪迈、幽默、诙谐、淡定,一样地袒露无遗。
如果说,林语堂以浪漫主义的散文笔调塑造了一位近乎完美、符合个人理想的文化巨人苏东坡、一位“月下的漫步者”,那么,郭宝平更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兼具文学性,他以考据为经,想象为纬,编织了一位现实生活中不完美的“人间东坡”,作者无意放大东坡的旷达与坚韧,也无意掩饰东坡的脆弱、纠结与局限,让烂漫天真的苏东坡重回人间,从眉山一路走来,至死依旧是少年。
这样的东坡,是月夜踏雪的飞鸿,是寒冬逆风的旅人,是“倚杖听江声”的幽人。在郭宝平笔下,在900多年前的历史场景中,苏东坡得以重新复活,他的血肉与灵魂,他的脆弱与伟大,唯其真实恳切,更能永驻人心。
亦侠:在儒释道精义的融会中锻造精神风骨
在还原历史真实、剖析复杂人性的同时,仔细梳理苏东坡精神风骨和思想境界的锻造与构成,是笔者在阅读郭宝平小说过程中的第二个深刻印象。
贬谪黄州以来,东坡以“此心安处是吾乡”来回应贬谪生涯的漂泊无常,既有孟子“穷则独善其身”、庄子“安时处顺”之意,又暗含禅宗“境由心造”的顿悟思想;在黄州作《赤壁赋》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表达了道家看待时间和宇宙变化的智慧;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凸显儒家“内圣外王”的入世情怀。儒释道精义的融合互济,让“乌台诗案”之后的苏东坡走出至暗的生命困境,实现了他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入仕以来,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苏轼从未放弃过任何一次经世济民的践行机会。王安石变法初期,苏轼目睹新法实施中的弊端,顶着“非议新政”的压力,写下《上神宗皇帝书》,面奏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在密州,遭遇旱灾、蝗灾,苏轼上书宰相痛陈新法之弊,吁请朝廷改弦易辙,为民请命;在徐州,黄河决堤,他与百姓一起筑堤抗洪,在城墙上搭起帐篷,坚守在现场……
如此种种,在苏东坡的人生旅途上,在郭宝平的细腻笔触下,桩桩件件,不胜枚举,已经成为苏轼生平事迹的日常,在他的从政以及贬谪生涯中,这些习以为常的言行举止背后,有儒者的担当与浩然正气,有佛家的慈悲与生命关怀,还有道家的抛却个人荣辱得失,无为而无不为的潇洒与超然之气。此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亦温文:在道德文章与人间烟火中彰显君子人格
如果说,“真”是苏东坡的性格底色,“侠”是他的精神脊梁,那么,“温文”二字,便贯穿了他一生一世的为人、为文和生活日常。无论居庙堂之高,或者处江湖之远,无论峨冠博带,或者草鞋布衣,苏东坡永远不改其温文尔雅的君子气度。郭宝平在小说中用大量笔墨,描绘了苏东坡平日里的待人接物、生活起居,在平凡、琐碎中,得以窥见苏东坡的文人本色。苏东坡的伟大,接着地气,因为温厚亲切,更显崇高。这是笔者对《苏东坡》的第三个深刻印象。
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写道:“其文如其为人”——高度赞扬了苏辙、张耒的为文与为人,曰其文风如人品,淡泊深远、含蓄蕴藉而难掩才华横溢。同样如此,东坡先生的为文,既豪放,又深情,如朗月入怀;他的为人,既随和,又温文,更似春风拂面;他的生活,在柴米油盐中透着浓浓诗意。
居茅屋草棚,处野岭荒郊,苏东坡一样可以在暗淡无光的岁月里找到亮点。在黄州,苏东坡发明“东坡肉”烹饪之法,赋《猪肉颂》,又作《东坡羹颂》,纪念他的创新饮食“东坡羹”;在惠州,研究出“东坡烤羊脊”的吃法,还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他写下劝农诗,教当地黎人从事农耕,他发明“玉糁羹”和生蚝去腥的新吃法,把粗茶淡饭吃出了“人间至味”。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深情款款的文与温文尔雅的人、柴米油盐的烟火与琴棋书画的诗意,大雅与大俗,就这么自然而神奇地融合统一在这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东坡居士身上,一诗一文、一餐一饭,一滴水足可以见太阳,行走在人间烟火里的苏东坡,依旧是彬彬君子,风华绝代。
总而言之,郭宝平的历史小说《苏东坡》,重史料,去神话,立人格。作者以史家笔墨、文学想象加人性洞察,复活了一位真实、真诚并且烂漫天真的历史人物形象;借助剖析儒释道三种文化对东坡侠义精神和思想内涵的影响与熔铸,诠释了东坡精神风骨的内在支撑;关注如同邻家大叔一样的苏东坡,在平凡普通岁月里的待人接物、生活起居、为人为文,描摹他的夫妻情、手足情、师生情、朋友情……以及他对于人世间一往情深的热爱。东坡先生的温文尔雅,已然融入了人间烟火,温暖了世道人心。通篇而言,小说完整揭示出了人间东坡的可爱、可敬与可亲。
可爱的是那份天真未泯的赤子心,可敬的是那份为民请命的侠骨义,可亲的是那份穿越苦难的温文气,可传承的,是人间东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