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情感律动与理性逻辑共鸣共振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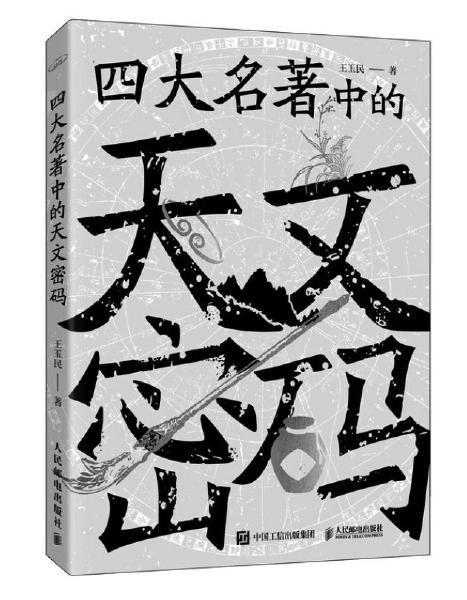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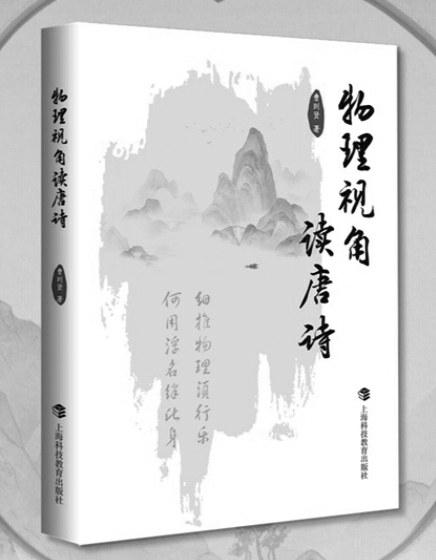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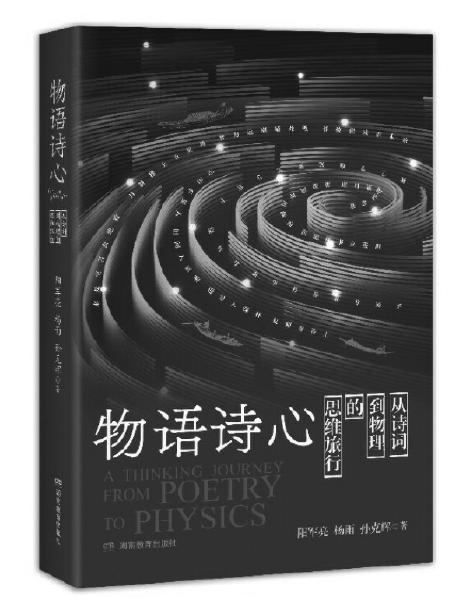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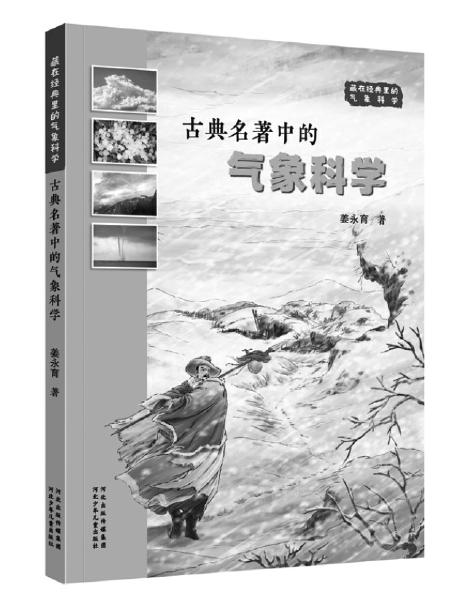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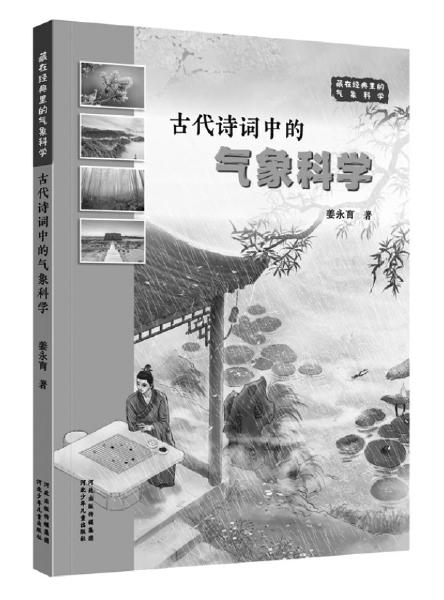

《古代诗词中的气象科学》内文插图。
当一首古诗不再只是意境的抒发,而成为一个关于自然现象的科学提问;当一部古典作品不再只是人物的悲欢离合,而呈现出宇宙运行与气候变迁的规律投影……文学与科学的交汇,便在阅读中悄然发生。
近年来,一种融合人文情怀与理性思维的跨领域阅读悄然兴起,相关图书也备受读者关注。它们打破了传统知识分类的边界,用科学视角回望经典文学作品,用文学语言激荡科学精神。这类图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激发兴趣、启迪思维的路径,也为他们打开了穿越古今、贯通文理的思维新维度。
文学成为科学入口
“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的诗句为何在成都能看见百里外的雪山?“东边日出西边雨”,这到底是哪种天气现象?“黄梅时节家家雨”,梅子黄熟就一定代表连绵阴雨吗?这些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的诗句,在《古代诗词中的气象科学》《古典名著中的气象科学》(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中都被一一“复盘”,成为科学思维的入口。“科学解读不是将文学‘拆解’,而是让文学‘发光’。当孩子们意识到诗中的美可以用科学方式解释,他们也会更愿意用科学方式理解生活。”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教辅编辑部副主任智烁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类图书不是简单的科普,而是用科学思维读懂古典。”智烁如是说。如《古代诗词中的气象科学》以杜甫的诗为例,作者从西岭雪山与成都的实际距离出发,结合春季降雨初晴后的大气透明度数据与能见度定义,推导出诗人确实可能在草堂窗边看到雪峰。“这种‘提出问题—查证资料—构建模型—得出结论’的方式,不只是验证了诗意的‘真实’,更是将科学精神融入文学阅读的全过程。”
在智烁看来,这套书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讲知识”,而在于激发孩子的提问能力、分析能力和跨学科思维。“它引导读者在阅读中不再停留于‘感动’与‘背诵’,而是进入质疑、论证、思辨的过程——这正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智烁谈道,这种不止步于“是什么”,而是深入到“为什么”“如何形成”的探究方式,可以让孩子们在熟悉的文学故事中体验到一种“科学侦探”的乐趣。
科学的理性与文学感性作品不仅注重文本分析,而且通过抽丝剥茧的科学分析,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不断提出新问题,带领读者探寻那些脍炙人口的古诗词、古典名著故事里被人忽视的科学知识,这也是读者深度思考的过程。
《古典名著中的气象科学》一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借萧让之口说出雪花的6种形态,作者对此产生了疑问,从我们常见的雪花形状到雪花形成原理,再到特殊情况下所形成的雪花形态,最后论证出雪花不止6种,古人“草木之花多五出,独雪花六出”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这种多学科思维的论证,对于少儿读者的思维锻炼是多角度、综合性的,启迪读者关注生活中的细节,勇于质疑,发散思维思考问题。”智烁说道。
科学视角理解文学
如果说从文学中“找出科学”是一次由感性走向理性的探寻,那么,从科学视角“重新理解文学”,则是一场从逻辑中生发诗意的回环。不少图书以此为基调,力图打开文学的“科学层面”,更唤起了读者对自然规律之美与宇宙奥秘之思的诗意感知。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在《物理视角读唐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中提出:“唐诗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辞章优美,还在于它是那个时代人类认识自然、感知世界、应对生存的结晶。”他指出,诗人不只是书写情感,更在直觉中揭示着自然法则。例如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在空间关系和大气反射层面实则暗含了对“逆温现象”的描绘;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恰是将重力加速度与人类视觉、错觉相叠加后的艺术表达。
“我们常说文学高于生活,而科学告诉我们,生活远比想象更奇妙。”曹则贤认为,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需要在逻辑严密中体验想象的跳跃。“物理不仅是解构的工具,它也能为文学注入坚实的支点。”在他的解读中,读唐诗不仅是理解古人的抒情方式,更是一次次情感律动与理性逻辑的共鸣。
同样通过科学逻辑理解文学的还有《四大名著中的天文密码》(人民邮电出版社)。该书系统梳理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中出现的日食、月食、彗星、大雨、星辰等天象描写,将“天人感应”“星占推理”一一转化为现代天文观测的综合视角。在人民邮电出版社科普分社编辑韩松看来,“科学与文学的结合,首先能让读者对科学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如古人对天象的理解常包含文化意涵与政治投射,但其中也不乏细致入微的自然观测,这正是我们与古人可以对话的入口。”
作者在解释天文知识时,都引用了充足的原著情节,比如,在行星与星宿两章,作者通过《三国演义》中对天象的描述和《西游记》中的各星宿神介绍了古天文中的行星和星宿体系。通过科学解读,不仅还原了文学的“真实场景”,更增强了读者的“历史在场感”。“真正打动读者的,不是空洞的美词佳句,而是当他们体会到古人所见天光与今日相通,他们就会在文学中发现生活的镜像。”韩松对此坦言道。
《物语诗心:从诗词到物理的思维旅行》(湖南教育出版社)进一步拓展了“文以载理”的路径。责编胡雅琳表示,该书定位是“思维方式读本”,核心不是知识的堆叠,而是帮助读者建立“像科学家一样读文学”的路径意识。书中通过对诗句中力学、热学、声学原理的分析,构建了一个“理工科思维下的文学地图”,让读者在文学中了解物理建模思维,在公式之外重新认识感性。
“我们不是让读者看到一首诗就去找公式,而是让他们意识到:每一个自然现象背后,既有情感的描述,也有世界的法则。”在胡雅琳看来,这种文理兼修的方法,用科学点燃对文学的热爱,用文学唤起读者感知科学的温度。
充分释放思维张力
采访对象一致认为当科学遇到文学的意义所在,便是“让思维不设边界,让认知走出课堂,让世界因阅读而被更深地理解”。
“人们常以为科学是现代的,古典文学是传统的,两者是遥远的。”智烁认为,这样的对立实则源于惯性的认知模式。当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解读古诗词、名著,经典的“高远”被拉回到日常的“真实”,读者不再把文学看作象牙塔上的咏叹,而是在那些千百年前的词句中,看见了可验证的自然现象、可追问的生活细节,“这正是科学的魅力——它帮助我们重返生活本身,也帮助文学重新落地。”
文学来自生活,也高于生活。但我们经常关注的是它“高于”的那一部分,而忽略了它是如何贴着生活展开的。智烁说:“当我们从科学角度去理解文学中记录的日月星辰、风雨霜雪,看到的是古人对自然的智慧、对生活的体察,尤其对青少年读者来说,能从这种解读中学会观察世界、热爱生活,最终建立起对文化的认同感和思维上的独立性。”这种从文本回归生活的阅读路径,不只打开了知识结构,更激发了思维方式的改变。
韩松也表示,科学视角确实为经典阅读带来新的可能。它一方面帮助读者理解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对宇宙的感知方式,另一方面也拓宽了文学赏析的趣味性维度。但他同时提醒,在阅读中要避免过度科学化,不要完全按字面去分析虚实结合的诗句,以免削弱原本的诗意张力。“文学中有留白与象征,有情绪的投射与想象的空间,这些不能简单地理解成物理现象。”
韩松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母亲的反馈,她的儿子读小学五年级,虽然《四大名著中的天文密码》并非少儿定位,但因语言生动有趣、内容通俗有思考深度,孩子竟放学就主动读。“这份主动,正是阅读最本质的动力来源。”
在胡雅琳看来,科学的介入不仅是知识的拓展,更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的激活。她认为,科学为文学注入了全新的时空维度,使古典作品中的空间感、情绪感、哲理感都发生了更新。她举例说:“如果我们从宇宙膨胀的概念去理解杜甫‘一览众山小’的空间感,那种震撼就不仅仅是地理的,更是宇宙尺度的;如果从量子纠缠去体会李清照的情感句子,那种思念就变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情绪联结。”这类解读,虽然带有想象,但恰恰在文学与科学的对话中释放了人类思维的张力。
在湖南师大附中的“名家领读”活动中,胡雅琳还观察到,学生们对《物语诗心》中提出的科学问题表现出超出预期的热情与好奇。“而这份好奇,恰恰是文学遇到科学带给孩子们最有价值的礼物。”胡雅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