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在文明互鉴中走出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自信之路》读后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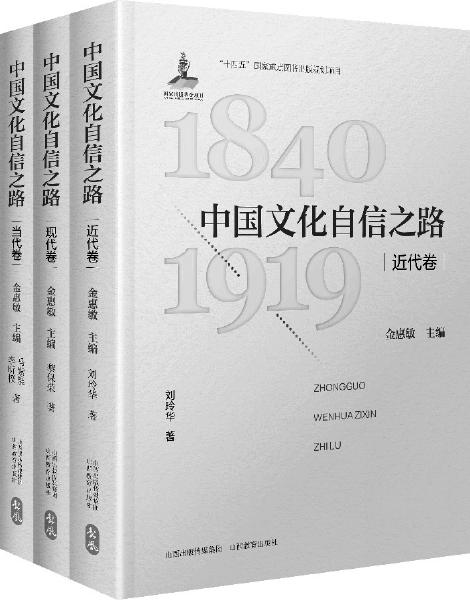
“文化自信”被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理解今日之中国最为核心,亦是今日之学术界最具多维视角的关键词之一。金惠敏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自信之路》三卷本丛书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首次完成了对近二百年中国“文化自信”思想流变的历史梳理,并深入探究了“中华文化何以自信”的内在逻辑。
应当指出,在“文化自信”的表述背后,其实预设了一个“文化自我”之存在,这一“文化自我”又关联于一个使其显化的他者之存在。正如主编金惠敏教授曾指出,“在‘文化自信’这个短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镶嵌着一个‘自’字,即一个有关‘自我’的观念,而处身‘文化’之中的‘自我’,实际上便是‘文化自我’”。这一自我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外物(尤其是他者)反观到“我”的存在,其本质体现为个体或文化间的对话性状态。
《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璞玉有华,贵在臻至。文化的自我确认始终伴随与他者的对话。以个体主体为例,作为有限性的存在,个体的特殊性生成了观念世界的差异,这些差异作为世界的不同侧写,相互碰撞,触发个体间的双向惊异与补足:人们正是在彼此的惊异中,发觉世界的多元呈现,拓展自身的认知边界。事实上,从穿行于安纳托利亚至爱琴海的黑曜石之路,到串联起东北、长江流域乃至可能的中亚地区的玉石之路,人类相互联结与交流的本能,早已编织起文明互鉴的原初之网。这也正是丛书选取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起始点的原因所在——当中华文化进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时,当“天朝上国”这个自视终极的文化图景遭遇另一个强有力的他者时,文化的自我怀疑、反思与再确认才真正成为中华文化的现实问题,激发其复苏文化的内生动力。《中国文化自信之路》的思想史梳理,实乃对中华文化何以重构自我主体的追根溯源。
只是,对话中的惊异常与恐惧相伴,这便是工具理性的内在张力:人们依托理性确立自我的边界而立身于世界,却也因此惯于排斥难以纳入其认知框架的异质文化元素——文化转型中守成势力的潜在排异倾向或根源于此;但正是在恐惧与对话的历史性共生中,中华文化何以自信的生成机制方得以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求索历程揭示,无论是文化自信所立足的文化自我,还是文化主体性所显化的文化主体,绝非某种静止的本质化特质——对人类这一有限存在而言,任何文化系统皆无法宣称其绝对完满——而是在差异对话中持续建构的动态过程。面对差异与对话的辩证关系,核心并非取舍,而在于承认其本体性共生:世界的无限丰富使差异成为认知的必然境遇;人们在惊异与恐惧中萌发的存在渴求,则使对话虽曲折却坚韧地延展为文明本能。可以说,正是有限性本身,推动人类作为自觉的有限存在者于差异与对话的无限场域中,实现自我超越。
在这一过程中,外来文化不仅是必然遭遇的结构性他者,更是文化主体实现自我扬弃的必要触媒。这绝非文化主体性的缺失,恰是其生命力通过辩证性吸纳得以强化的明证——这种强化既拓展了文明的解释视域,亦淬炼了其意义生成机制。至于何种元素可以成为充盈文化自身的建设性质料,何者又需经批判性扬弃,则取决于具身的文化环境,取决于既已绵延至今的文化主体之内核,即文化主体的价值判断与适应时代变化的实践本身。面对时代转型,这种价值判断必须立足于使文化主体持久生成、自主存续的内生性逻辑,这正是《战国策》“战胜于朝廷”所具有的当代启示——真正的文化感召力,生于内源性的强大,而非强迫性的征服。唯有文化主体建构的持续深化,文化自信力方能升华为跨文明可通约的认同力量,在文明互鉴中彰显普遍价值。这便是今日之文化自信所秉持的道路:在坚守社会主义底色之价值判断的同时,既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可以说,《中国文化自信之路》以“文化自信”的思想史为经纬,重新解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文化逻辑;更为深刻的是,通过中华文化复兴的实践范本,确证了人文学科的本体论价值——人文学科的意义是对元价值,即对价值“可以可能”以及“何以成立”的探索与确定,相较于军事或科研的显性效用,人文科学关注的是价值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即不同文明如何理解自身、回应他者的过程,并最终在多元价值叙事的对话中熔铸文化主体的价值自觉。正是这种使价值从“可能”走向“自觉”的生成性力量,让人文学科成为文明演进不可替代的意义引擎。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自信之路》向我们宣告:今日之时代,必将是一个向世界敞开的时代。所谓面向世界,既非盲目追随他者,亦非固执于封闭自我,而是各个文明主体突破认知阈限,在历史性的对话中淬炼自身——既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他者生命力的底色,更以创造性转化充盈文化主体的精神谱系。面对个体存在的有限性,我们虽无法复现消逝的历史现场,却能以超越时空的意义星丛,“尽可能地向我们提供一些更好的和更高尚的东西”,使世界文明的万花筒折射出更具生命力的色彩共同体。也正是在文明星丛的色彩共生中,我们才得以理解,何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民族的。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