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堂永固——宋金砖墓仿木研究》
仿木研究不再“盲人摸象”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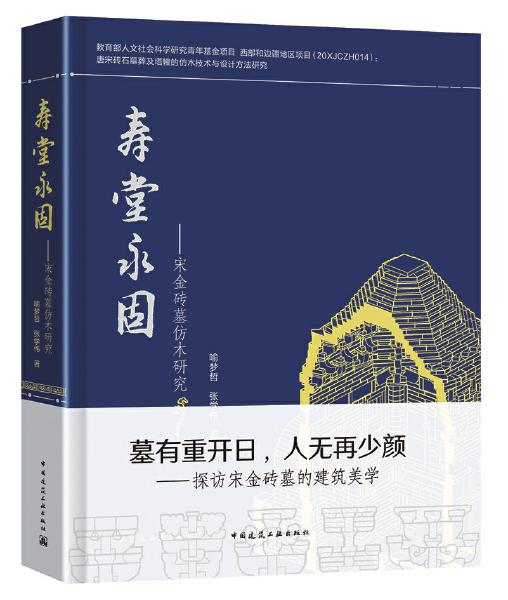
盲人摸象是个人尽皆知的可笑故事,但对理解这本《寿堂永固——宋金砖墓仿木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来讲,又是一个最生动、准确的参照系。比照于研究工作来说,大象是需要认识的对象,描述它的样子是核心任务,回答的角度则来自不同学科,但最终我们掌握的是大象的几个局部特征,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大象本身。
宋金砖墓中的仿木现象也是个亟待认识的对象,它引发了仿木是什么这个问题。从哪些学科来回答呢?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艺术史。方法论是什么呢?原子论、整体论,抑或二者的整合。该采取什么方法?历史考证、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筑场域理论、建构主义和图示分析方法……由此得到了历史学家眼中的制度变迁、风俗流转、阶层下渗。考古学者眼中的区期分界和样式分型,建筑学家眼中的空间意向和构造设计,美术史学者眼中的历史原境复现,显然,这些局部认识的加和并不满足我们解释仿木现象的诉求,该怎么办呢?下面试做分析。
我和喻梦哲老师近年来多次探讨建筑考古学是什么的问题,大概达成了三个粗浅的认识。
第一,考古学是个对象性学科。现有学科可以分为对象性和角度性两类,后者针对对象某一属性展开,如物理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学等;前者则以人类的历史实践为材料,如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等。
第二,整体性与角度性的关系。如果我们只关注作为组成部分的角度性、反倒忽略了作为整体的对象性的话,就会像分别“摸象”的盲人一样,在事实上“杀死”了那头大象。对于建筑考古工作来说,应该确保对象性学科统领角度性学科,就像建筑师一样,他要兼顾择址备料、结构选型、施工管理等各方面内容。在他的组织下,一座仿木砖墓最终顺利毕工,并且满足了方方面面的要求,这就是整体之于角度的关系。
第三,对象性学科的方法论是整体论。在考古学实践中涌现的首先应是一种整体论特质,譬如在田野考古中,组建多学科合作的课题组是大势所趋,这类机制一旦建立,往往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这本书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对象性与整体论的自觉上。
首先是对象性与角度性的自觉区分。因为有了这组关系的警醒,作者才能超越以往角度性学科的层次,跳出各个角度的局限,觉察到盲人摸象的危险,主动追求对象的完整性——全书一到七章为总分结构,头两章为总论,探讨了从仿木行为、仿木对象到仿木现象的认识发展过程,介绍了引发仿木现象产生、发展的营造传统、伦理观、生死观、技术储备、丧葬制度等内外因素,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视野、抱负与学力,完全超越了单个学科的局限;三到七章分别对宋金仿木砖墓的内容组织、空间营构、设计思路、加工方法、比例控制与构图规律展开论述,算是对之前理念的实践。
其次是整体论与原子论的自觉警醒。作者始终兼顾各种相关学科,吸收、引介其代表性成果,使得全文丰富、多元,当然,考古学对本书的贡献尤其关键。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建构起的分类型、立谱系的工作范式利于高效处理实证材料,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古学以年代学方法落实了案例的区期特征和分布规律,同样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严谨的时空框架指引,确保本书在宏大的框架下准确、高效地运用海量材料,为我们勾描出宋金时期满含趣味与深情的营坟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