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标注进城市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2-08-26
《上海文学散步》这个书名,一眼看去,准有人会错了意,把“散步”当成一种已然习惯了的比喻性说法。可它本是脚踏实地的一个词,这本书就用它原来的意思,寻访现代文学在上海这个都市空间里的遗迹。
当然,一个地方有五六处遗迹,也大可满足参观游览的兴味,不过比起来,就没有那么丰富和复杂,丰富、复杂如眼前这本书呈现出来的。正因为丰富和复杂,要呈现出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需要案头功夫和脚下功夫的互相结合。做文学研究的专家、学习文学的学生,只做纸上漫游,不迈出文本的大门,不走进嘈杂的街头,不用脚,或许可行;“散步”的作者,却必须用脚,但“散步”之前、之时、之后,也需要材料文献的功课,不做好功课,脚都不知道往哪里迈。
作者在这座城市里穿行,从现在的空间走进历史的空间,走进我们熟悉的、模糊的和陌生的地方:你知道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但未必知道创刊地在法租界吉益(谊)里;你大概知道陈独秀1932年在上海被捕,但大概不知道他之前两年化名隐居于一条破烂弄堂,叫永兴里;你路过虹口区的一所普通学校,澄衷高中,或许会想起它是昔日的澄衷学堂,却未必想得到百多年前,这里有个学生,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胡适;你当然知道鲁迅居住的大陆新村,也知道他常去的内山书店,那应该也知道,他到上海,先住的是景云里。要是你还知道得更多,就会想象一些情景:茅盾、叶圣陶、柔石也住景云里;冯雪峰避祸在茅盾家,站在晒台上,可以看到斜对面鲁迅的卧室兼书房,晚上过去聊天谈心,时间长的时候有三四个钟头;鲁迅搬到拉摩斯公寓,冯雪峰一家也随之住进了公寓的地下室;你读过《春风沉醉的晚上》,而未曾留心,这是郁达夫住民厚南里时写下的,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是他熟悉的日新里,位于这些年才繁华起来的北外滩……
这本书追索48位作家和学者在上海的踪迹,他们生活、工作、交游之所,如密密麻麻的点,把这些点连起来,就是一幅上海现代文学地图。你把它当成一幅旧地图,借助它进入昔日的空间和时间,触摸质感的历史,感受其气息,想象其情境。无疑,它有这样的功用,但这只是一层。一个现在的写作者,在现在的都市里,靠轨交、公交和脚步划出一条条线,合成的,是现在的地图。它是新划的,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地图,它勾连历史上那一个又一个点,标注它们的旧时样貌,也标注它们的现时状况。它是新旧层叠的地图,是历史感和现实感交织的地图。因为层叠和交织而生成的缝隙、深度,你就很难把它当成是平面的,单纯的旧,或单纯的新。
划这样一幅地图,需要努力,需要顽强。它不仅要标注那些存留的、保护的,也要标注那些残破的、拆毁的,不仅标注胜地,也要标注废墟,不仅标注承续,也要标注消失。它要顽强地把文学标注进城市,把过去标注进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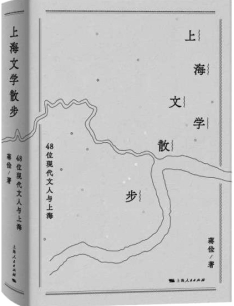
《上海文学散步:48位现代文人与上海》
蒋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