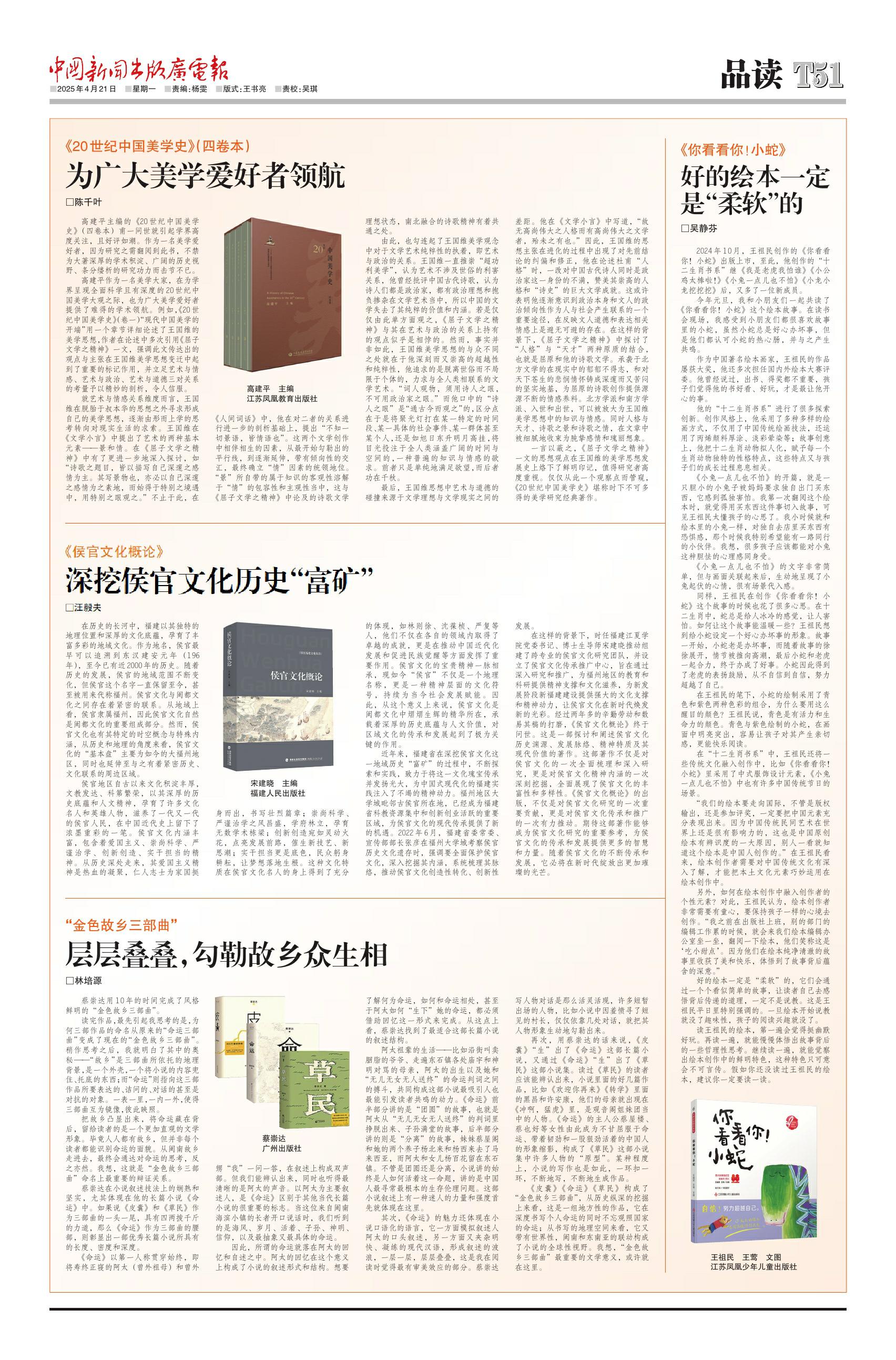-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20世纪中国美学史》(四卷本)
为广大美学爱好者领航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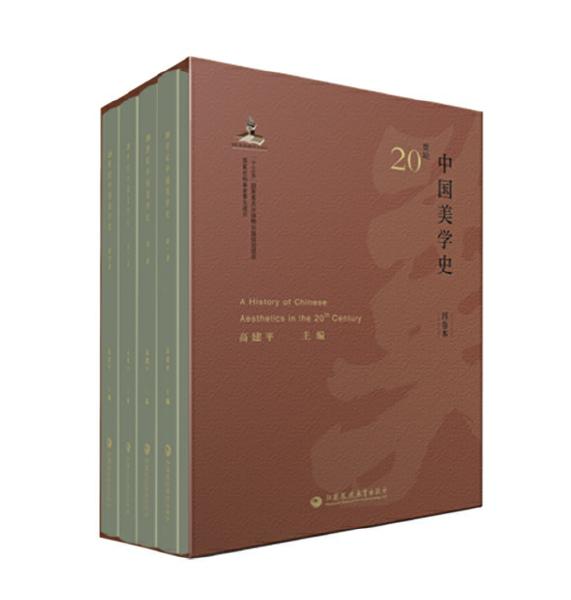
高建平 主编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高建平主编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四卷本)甫一问世就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且好评如潮。作为一名美学爱好者,因为研究之需翻阅到此书,不禁为大著深厚的学术积淀、广阔的历史视野、条分缕析的研究功力而击节不已。
高建平作为一名美学大家,在为学界呈现全面科学且有深度的20世纪中国美学大观之际,也为广大美学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学术领航。例如,《20世纪中国美学史》(卷一)“现代中国美学的开端”用一个章节详细论述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作者在论述中多次引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强调此文传达出的观点与主张在王国维美学思想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标记作用,并立足艺术与情感、艺术与政治、艺术与道德三对关系的考量予以精妙的剖析,令人信服。
就艺术与情感关系维度而言,王国维在脱胎于叔本华的思想之外寻求形成自己的美学思想,逐渐由形而上学的思考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求索。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提出了艺术的两种基本元素——景和情。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有了更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如“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不止于此,在《人间词话》中,他在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基础上,提出“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两个文学创作中相伴相生的因素,从最开始勾勒出的平行线,到逐渐延伸,带有倾向性的交汇,最终确立“情”因素的统领地位。“景”所自带的属于知识的客观性溶解于“情”的包容性和主观性当中,这与《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论及的诗歌文学理想状态,南北融合的诗歌精神有着共通之处。
由此,也勾连起了王国维美学观念中对于文学艺术纯粹性的执着,即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王国维一直推崇“超功利美学”,认为艺术不涉及世俗的利害关系,他曾经批评中国古代诗歌,认为诗人们都是政治家,都有政治理想和抱负掺杂在文学艺术当中,所以中国的文学失去了其纯粹的价值和内涵。若是仅仅由此单方面观之,《屈子文学之精神》与其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持有的观点似乎是相悖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国维美学思想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深刻而又崇高的超越性和纯粹性,他追求的是脱离世俗而不局限于个体的,力求与全人类相联系的文学艺术。“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而他口中的“诗人之眼”是“通古今而观之”的,区分点在于是将聚光灯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某一具体的社会事件、某一群体甚至某个人,还是如旭日东升明月高挂,将目光投注于全人类涵盖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的,一种普遍的知识与情感的欲求。前者只是单纯地满足欲望,而后者功在千秋。
最后,王国维思想中艺术与道德的碰撞来源于文学理想与文学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在《文学小言》中写道,“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因此,王国维的思想主张在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先前结论的纠偏和修正,他在论述杜甫“人格”时,一改对中国古代诗人同时是政治家这一身份的不满,赞美其崇高的人格和“诗史”的巨大文学成就。这或许表明他逐渐意识到政治本身和文人的政治倾向性作为人与社会产生联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反映文人道德和表达相关情感上是避无可避的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探讨了“人格”与“天才”两种原质的结合,也就是屈原和他的诗歌文学。承袭于北方文学的在现实中的郁郁不得志,和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铸成深邃而又苦闷的坚实地基,为屈原的诗歌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感养料。北方学派和南方学派、入世和出世,可以被放大为王国维美学思想中的知识与情感。同时人格与天才、诗歌之景和诗歌之情,在文章中被细腻地收束为肫挚感情和瑰丽想象。
一言以蔽之,《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的思想观点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烙下了鲜明印记,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仅仅从此一个观察点而管窥,《20世纪中国美学史》堪称时下不可多得的美学研究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