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栗往事惹乡思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1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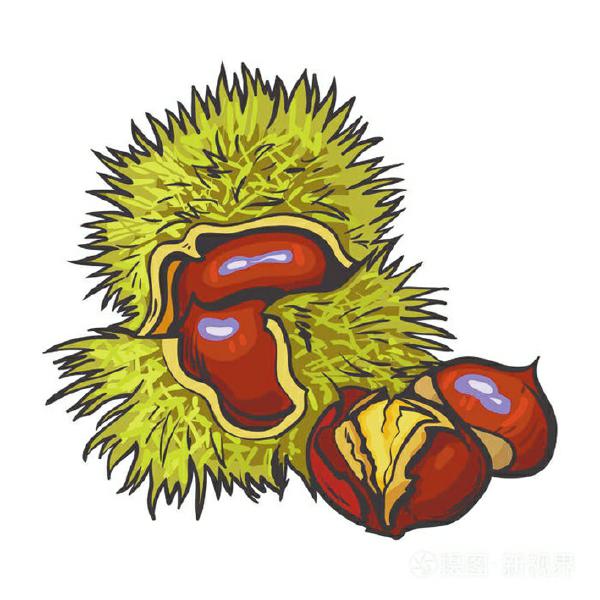
资料图片
故乡盛产三种栗子,分别是“板栗子”“毛栗子”“朱栗子”。
这三种栗子中,名气最大的是“板栗子”。故乡地处皖南山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适合“板栗”的生长,所产“板栗”以果实饱满、栗香醇厚著称,是上天赐予的绝佳美味,更是家乡一干土特产中的上品。“板栗”树高大粗壮,生命力强胜持久,也是三百里泾川大地上壮美的风景。
“毛栗子”似乎算是袖珍版和山野版的“板栗”。它自然生长在青弋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中,树枝细且矮,属于灌木一类,又较一般的灌木稍高且粗。或许是因为生在野外,自生自灭,成长艰难,其果实比起“板栗”来就要小很多。我想,其名“毛栗子”中的“毛”字,可能正是为了说明了其“小”吧。
“朱栗子”(也叫“珠栗子”)在植物学中的学名叫“苦槠”,是南方山区独有的栗子种类。“槠”发音同“朱”“珠”,而字又不如后两个好记好写,所以家乡人就干脆叫它为“朱栗子”了。它的果实椭圆,涩味较重,无法直接食用,但可以加工成豆腐。很久以来,“朱栗子”豆腐就是家乡一道传统佳肴。
这三种栗子像星星一般点缀了我童年的岁月苍穹,让那一段平淡的日子显出了温馨的亮色。
山翠林绿,气候温润的故乡,花草树木,万物生长。“板栗”树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东南西北乡,每户农家的前场后园里,都会种有几棵“板栗”树。春夏绿叶扶疏,生机盎然,深秋时节,果实成熟,栗香飘逸。而我从小生活在县城,青石街道,砖木平房,家里没有空间植树养花,“板栗”之类的农产品自然也就无法自给自足。好在我的老家查济村就是“板栗”主产区,所以,每年“板栗”上市之际,总会有亲朋好友给我们捎来一些。“板栗”个个饱满,深褐色的外壳油亮可人,煮熟或者剥壳后烧鸡、烧肉,都是极具诱惑的乡土大菜。
7岁那年冬天,父母带着我回了一趟查济,看望生病的奶奶。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病床上的老人家拉着我的手,像是愧疚似地说,孙儿呀,也没啥好吃的给你,那几棵“板栗”树今年结得也少。明年吧,明年早点来,我给你打“板栗”吃。听她这么说,我便特意到屋后园子里看了看那几棵“板栗”树。繁华落尽之后,高大粗壮的树上只剩下铁打铜铸般的枝丫,披着冬日的暖阳,凌空倔强地伸展着,显示出苍劲的生命力。又似乎是摊开手臂,向我做着无奈的表情。它们没给我以果实,却以这样的造型带给我震撼。第二年冬天,奶奶驾鹤西行,没能吃上她老人家亲手打的“板栗”,成了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那以后好多年我都没有回过查济。直到前几年我再次踏上故土,曾经雕梁画栋、青砖黛瓦的祖屋早已不复存在,周围也已不是当年的风景。在友人的引领下,我找到祖屋原址处的那片园子,一眼便看见了几棵熟悉的“板栗”树仍然坚定地伫立着,虽然容颜老迈,却仍然透出一股苍劲凛然的生命气质。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只见过一次面的奶奶。此时也已过了栗子的收获时节,我没能体验从高高的树枝上打下“板栗”的快乐,只在树下拨开落叶,捡拾到了几颗。我小心翼翼地剥去刺壳,把两粒深褐色的果实放进口袋,像是收藏起过往的岁月。
层林尽染的季节,上山去打“毛栗子”,是我少年时代最为快乐开心的事情之一。不用上学的星期天里,只要天气晴朗,家住西门口的一群小伙伴,就会邀约着三五成群拎着个小竹篮或是布口袋,揣一把剪刀,徒步七八里路,到城东的山上去打“毛栗子”。一到山里,我们便如鸟出笼、鱼入海一般,撒开了欢。
“毛栗”树长得不算高大,又杂生于满山遍野的草木之中,所以,要于万绿丛中准确地寻到一棵(丛)果实累累的“毛栗”树也很是不易。被树枝剐破衣衫、被刺扎破手指,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更有时会一脚踏空,摔个四仰八叉。
和“板栗”一样,“毛栗子”的果实也是被坚硬的带刺外壳包裹着,需要用剪刀把它从树枝上剪下来。为防止被刺扎,我们会戴上厚厚的帆布手套。有次在山上跑上跑下、跑东跑西,也没找见一棵栗子树。正当心烦意乱时,猛然发现前方一棵树上挂满了“毛栗子”,情急之下,忘乎所以,猛扑过去,直接出手将它们一颗颗揪下来。即便有厚厚的手套护着,手指还是被刺扎出斑斑血迹。但是收获的喜悦、“毛栗子”甘甜的诱惑使我们完全忘了疼痛。
“板栗”果实较大,可单独煮、炒后食用甚至生吃,更可以用来烧肉、烧鸡,肉香与栗香交融,软糯和酥烂并存,那绝对是一道美味。但“毛栗子”就不行了。它太弱小,若是剥去外壳和肉同煮,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煮化了。所以,它只能当着零食解馋。我们把打回来的“毛栗子”摊开在地上,晾上几天,再用剪刀小心翼翼地一个个剥去带刺的外壳,洗干净后放进锅里用水煮熟。有一年“毛栗子”长势特别喜人,连续几个星期天的采摘,我收获的“毛栗子”竟装满了一只小水缸。因为来不及剥壳,便堆在缸子积压了几天,再看时,原先青绿坚硬的刺壳已变得枯黄酥软,许多果子已经从壳里探头探脑几欲磞出。用棍子在缸子搅几遍,壳和栗子就自然分离了。这不亚于一个伟大的发现,从那以后,每每从山上打回“毛栗子”,我不再急于剥开,而是将它们堆在缸里,沤闷上几天,让它们先来个“自我了断”,再把它们倒在地上,在上面用重物稍一碾压,一个个褐色的小栗子就破壳而出了。省了很多气力,也避免了在剥壳时被刺扎破手指。
“毛栗子”生吃脆甜,满口清香;煮熟后再吃,软糯似饴。吃的时候用不着剥壳去皮,就囫囵个地扔进嘴里,连皮带肉,嚼得津津有味。前几番是栗肉的香甜,当栗子嚼完后,便是牙齿和脆硬的栗壳在口中撞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宛如美食浪漫曲的尾声乐章,回味无穷。
有时我会在口袋里装上一些煮熟的“毛栗子”,带到学校和同学们分享。还应他们要求,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也少不了添油加醋地描述上山打“毛栗子”的乐趣。那些没有上过山的同学,在被美味迷醉的同时,更是对踏遍青山打“毛栗子”这样充满野趣的活动充满了向往。有几位同学便在此后的时间里,加入到了我们上山的队伍,体验了一把劳动的快乐,更收获了甘甜的果实。
而学名“苦槠”的“朱栗子”,不像“板栗子”“毛栗子”那样,把自己深藏在带刺外壳之中,而是只披一件由青色渐变为褐色的外衣,从春夏到仲秋,在枝头迎风雨看日月,不炫耀,不争艳,落到地上,被人捡拾了,就会被加工成盘中餐,被人遗忘了,便化作尘泥护草木。
“朱栗子”虽苦涩,但它富含的淀粉成分却是做豆腐难得的材料。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人们把采摘回来的“朱栗子”用水浸泡后磨成浆,再经过沉淀做成豆腐。于是奇迹出现了!豆腐竟没有一点“朱栗子”原先的苦涩,只有淡淡的草本滋味,爽滑可口,深受百姓青睐。深秋时节,大街小巷会传来阵阵“栗子豆腐、栗子豆腐”的叫卖声,多少年来,这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遗憾的是自从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作以后,多年来没有再尝过这一道美食。听说现而今它仍然是家乡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佳肴,我便想着一定要在合适的时节回去大快朵颐。这既是品尝美食,也是品味岁月。
故园栗栗滋味浓,时光太匆匆。眼下又到了栗子的收获时节,我又一次想起了家乡,想起了查济祖屋后院的那几棵“板栗”树,想起了五里岗深山里的“毛栗子”,还有别具风味的“朱栗子”豆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