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视角讲述山乡巨变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4-08-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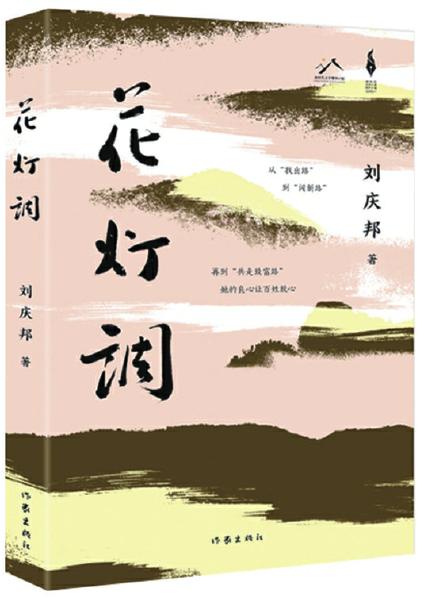
刘庆邦的《花灯调》(作家出版社)聚焦贵州深度贫困地区的高远村,以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为主人公,讲述了一个“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
《花灯调》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外在视角写国家意志。小说的主体放在了外界对高远村脱贫攻坚的助力上,突出表现了国家意志在深度贫困地区实现脱贫之路上的重要性。小说写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各相关部门的配合,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的宵衣旰食,夏方东、尚应金、周志刚、秦希明、韩二哥等基层干部和乡村骨干的艰苦奋斗,规划师、热心企业家等社会力量的支持。这种合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注脚。
文学创作毕竟不能仅看题材选择、价值站位、历史意识,更要看艺术成色。《花灯调》在这方面的一个大胆尝试是采用外在视角。所谓“外”有两层意思,一是叙述者以观察者的身份打量主人公向家明和高原村,二是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主人公向家明以外来者和驻村第一书记的双重身份处理与高远村的关系。《花灯调》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作家在小说中不直接出现,而是若隐若现有个观察者的影子。叙述者一方面写高远村的贫困和反贫困,一方面塑造灵魂人物向家明,写她的怕与爱、责任与难处、委屈与豁达。这种外在观察者视角的选择,一方面体现出老作家对当下乡村变革略感隔膜,试图通过写作策略调整弥补短板的潜在写作心理,同时又是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体现出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再看主人公向家明,当她看到留守儿童王安新家的凄凉光景时,她的母爱和责任心被激发出来,心甘情愿投身脱贫攻坚事业。尽管如此,她始终是外在于高远村的,她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自我与高远村、与脱贫攻坚事业的关系。
在高远村,向家明有不适应,有小心思,还有几次委屈地大哭、情绪崩溃;她喜欢猫猫狗狗,又害怕狗、怕老鼠,无法完全接受艰苦的条件。这是多么正常,多么富有人间气息。从这点上看,《花灯调》是半个多世纪前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回响,只不过后者是以人格化的方式呈现了两种文明的碰撞与冲突。这种碰撞与冲突同样构成了《花灯调》小说的张力。
小说在表现向家明真实感受的同时,着重呈现了这个外来者目光的转变,勾勒出一道人物弧光。从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到与深度贫困地区的乡民血脉相连,向家明在与他者的相遇中,完成了一次自我再生。这是《花灯调》的核心主旨与高远立意。心理落差的消弭、情感距离的缩短、认知隔膜的打破,背后是向家明个人意志的坚定。这种设置的背后是作家对山乡巨变成因的思考:国家行动与个人意志的交叠是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