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亲爱的人们》:呈现乡村振兴的文学新样本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4-0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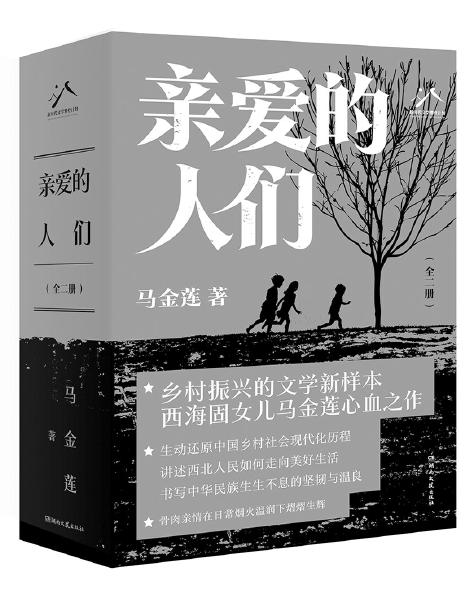
《亲爱的人们》为鲁迅文学奖得主马金莲费时多年创作的心血之作,全书80余万字,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重点扶持项目、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出版前全文分别节选首发于《中国作家》《芙蓉》《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朔方》《黄河文学》多家权威文学期刊。
作品结构类似《人世间》,通过讲述马一山、祖祖、舍娃等一家五口的人生命运故事,以真挚饱满的情感、细腻生动的语言和坚实丰厚的乡村生活经验,真实描绘中国最贫困地区西海固人民逐步摆脱贫困、追赶新时代步伐、走向美好生活的历史图谱,生动还原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亲爱的人们》
马金莲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近日,马金莲新作《亲爱的人们》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该书的作品特色、艺术价值进行深入研讨,认为它是兼顾文学性、艺术性的主题作品突破之作,也是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重要收获。以下是与会部分专家的发言摘登。
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马金莲在小说叙事上精细、绵密,一如既往,更显老到和成熟,更有大作品的正大气象。她坚持写自己最熟悉的土地,就是西北最深远的乡村。她的创作更加自觉地呼应时代的召唤,写出了接续奋斗,既有一致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又有新一代的求变的要求,包括观念上的变化,有的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去努力,更多的是为了家乡的变化去奋斗。她在写当下乡村时,自然地把乡村发生的新变化都写出来了,手机、网络、电商等情节、概念,包括与之相关的故事,更有扶贫和易地搬迁这些新时代所具有的更加生动、更具时代特性的故事。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一鸣:《亲爱的人们》是以近于原生态的乡土中国叙事,诗性探秘民族性格、民族心理,艺术透视历史进程、时代巨变的难得佳作,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硕果。
在不变与变、日常与宏大、地域性与普遍性三组关系中,作品体现出了特质,散发着金光。马金莲通过对凡人小事的书写,还原了故土农人独特的生命状态和生活形态,呈现出一幅幅独特、深刻的乡土人生图景,传达了作家对乡土中国文化的流连、慨叹与祈愿,对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礼赞。她采用散点透视笔法,勾勒出一幅西北乡村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作品在描绘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以现代意识烛照故土现实,描绘了普遍性的对于命运的挣扎,顺应时代变迁,勇于改变现实、勇于探索未知,向着未来奋力奔赴的精神。
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亲爱的人们》既是十分小说化、文学化的长篇小说,同时又是地域特色鲜明、农民生活鲜活、时代烙印鲜亮、主题自然生成的主题出版物。主题是在小说化、文学化、地域性、农民个性、生活灵性中自然凸显,是由人物、地域、鲜活生活、大量情节和细节构成的主题,而不是主题在指挥、调动着人物和生活。
马金莲的作品以人物命运发展变化为中心,故事绝大部分的笔墨就是围绕马家的五口人,然后由此辐射。他们在奔向小康过程中,个人走过的路、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物的命运。整部作品是由大量的生活情节和细节编织而成,但是被马金莲写得活色生香。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贺绍俊:《亲爱的人们》更注重日常生活的变化,以马一山一家人的故事为主线,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变化。马金莲着眼于写新事物、新现象,如何跋涉千里进入西北乡村,又进入人们日常生活肌理,这属于史诗性的架构,但马金莲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她一如既往地沉浸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不刻意追逐宏大的事件。她是贴着生活的真实情景去感知和书写,这样的写法更能真实反映西北乡村的现实。
在作品中,马金莲不是立足于显眼的成绩来写西海固脱贫,而是立足于漫长与艰辛来写乡村普通人的韧性和憧憬,这就一下子与大量写乡村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小说拉开了距离。《亲爱的人们》最突出、最独特的特点就是将乡村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乡村日常伦理进行审美化书写。小说不是刻意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却成为乡村振兴主题作品最有说服力的文学文本。
《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亲爱的人们》是近些年来长篇小说重要的现象,是向生活致敬、向乡村致敬、向乡间的人们致敬的作品。从书名可以看得出来,马金莲这样的作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生活中的人充满敬爱、崇敬的心情,也是一种对时代充满感恩的态度。乡间的人们确实是踏踏实实地生活在现实中,饿了做饭,天黑上炕睡觉,夏秋两季收割,冬天趴在热炕上,这样的生活样态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了他们新的内容。作品就是以这个为中心,看似波澜不惊的场合,确实是淬炼人、锻炼人、成就人的时代。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柳建伟:这是一部有着清晰年轮的,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漫长时段,中国农村特别是偏远的西部农村,伴随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非常缓慢展开的、可信度很高的文学时代白皮书。中国农村和中国变化40年间展示得这么细且有辨识度,就是这本书了:交通工具从蹦蹦车到小轿车,通讯工具从喊到座机再到智能手机,政策变化从分田到户直到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全方位可感可触忠实生动地记录下来了。
马一山一家五口被解剖的那么细,可以称之为西海固农民的秘史和心灵史。马一山和马一山女人有西海固农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三个儿女的日常生活机遇确实都打着时代的烙印,各自都有自身的机遇,作家写出了各自心灵的深度。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亲爱的人们》是一本令人意外的、清新的,甚至反传奇性的小说。作品继承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写作的优良传统,从内部的悸动写西部的山乡巨变,具有较长的时间长度和厚度。
马金莲对人物形象的雕刻也十分到位,既写出了人物的棱角与质感,也写出了日常生活的真实感与生动性。长篇小说的开头很容易让读者有一个爬坡的阶段,但《亲爱的人们》开头即是高潮,因为里面呈现的矛盾关系太多了,长期积累下来的生活习惯、人物关系、家族关系、环境因素等带来的矛盾关系,但这就是生活本身。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亲爱的人们》完全是把农民作为叙述主体,这也是作家把农民生活史写得很彻底的原因。整个作品的结构是人物推着事件走,不是事件带着人物走。在朴素风格与艺术表现张力的关系上,作品处理得非常好,它把一个村庄写出史诗性的味道。鲜活的群众语言和精确的叙事逻辑也处理得非常好。在方言叙事上,作品开头就用几个词概括这个时代的特色和变化,开篇就给人广阔幽深的语言博物馆的感觉,作为小说的入口,我看小说的时候有一种对语言的放心和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刘大先:马金莲《亲爱的人们》继承了《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一类作品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品细致又绵长,风格细腻委婉又不乏恳切的反思,它是西部山区的风俗画,也是乡土社会的史诗,还是新世纪的喜剧。作为乡土社会的长远叙事,作家热衷于写小人物的失败或者写英雄的成功,但这部作品是普通人的叙事,写的是好坏参半的普通百姓的生老病死与爱恨恩怨,写的是中国式的父母与儿女之间情感的交织,既有压抑也有体恤,既有狭隘也有宽容,有恨,但更多的是爱,这种患难相帮、彼此扶持的情谊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作品中的时间流逝,叙事节奏很自然,它并没有依靠外部的社会事件标识时间,而是用“羊圈门”自身的地理地貌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来体现。《亲爱的人们》的叙述中有一种理解所有人的悲悯,也有理解一切生活选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达到了某种大爱的情怀和开阔的境界。
中国作协创研部发展研究处处长聂梦:《亲爱的人们》完成了两个对接,一是与时代的代表性文学叙事对接,它从地域出发,历史性地与当代中国生活、中国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件密切关联,乡村巨变和现代化发展的线索像水印般隐在文字下面;二是与深远厚重的文学脉络对接,在家国视野下,小说以新背景对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进行创新和创造。
这部有着工笔画触感的作品以细节为本体、以生活为主体。我们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系列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事物,而常见于同类题材中的外视角被发展性内视角取代,所有动机都源于生计,每个人奔向美好生活的努力都建立在眼下的舍弃和遥远的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