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回“老盐工”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3-0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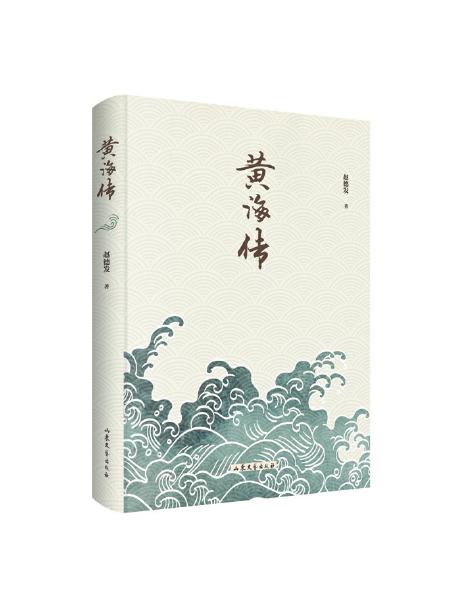
在我的家乡,多数老辈人没见过大海,盐是他们认知大海的媒介之一。做饭要用盐,腌咸菜要用盐,不吃盐就没有力气,他们认为是东海(家乡人至今还将鲁南苏北的海叫东海)给了他们能量,所以对盐十分珍重。我小的时候多次看到,有人想过过酒瘾了,到小卖部掏出一毛或两毛的票子买点酒,端起小黑瓷碗一口气喝光,从柜台上捡起售货员撒落的一粒盐做酒肴。有人在啖盐之前,还特意用拇指与食指捏着那个晶莹剔透的正方体向别人强调:这是海味儿!那时的食用盐都是原盐,在现今的商店里已经见不到了。
我爷爷曾经是个盐贩子。他年轻时从家乡收购花生油、花生米之类的土特产,用一头骡子驮上向东海走,路上住一宿,第二天上午到青口(今江苏赣榆县城)卖掉,再买一驮子私盐,到临沂卖掉后回家。这一趟买卖,共用3天工夫,能赚一块大洋。爷爷老了,还多次向我讲海,讲贩盐经历。他讲他看到的晒盐场面,端着烟袋啧啧称奇:“清水里捞白银,你说有多奇怪!”
爷爷离世后的第五年,我到日照工作,参观过这里的盐场。那些老盐工,在风吹日晒之下劳作,特别辛苦。看到他们晒出的卤水变成雪白的盐堆,我由衷赞叹。
挂职期间,我有时独坐海边,脑子里生出一些古怪念头。看着渔民们一年到头在海里谋生活,我想,地球上的生物是分为两类的,一类以海为生,例如渔民、鱼、虾、蟹、螺等等;另一类以土为生,例如农民、庄稼、草木、牲畜等。这是两类本质上不同的生物,很值得比较和研究。看到渔民忙忙碌碌却收获不多,听他们讲海里的鱼一年比一年少,我暗暗惊慌:他们没鱼可打了,会不会去争夺农民的土地种庄稼?我又马上嘲笑自己:咳,你什么时候能把农民子弟的尾巴彻底割除?
30年下来,我那条尾巴不断变短变小,对大海渐渐亲近。我努力认知海洋,深入了解她的历史与现状;我研究海洋文明,试图弄清其内涵与外延。我接触到许多生活在海边的人,听他们讲海上的故事,曾随渔民出海捕捞;我发现了海边的许多新生事物,一次次去采访、考察,感受海洋在新时代的律动。
这30多年,我的人生轨迹是从山岭到海洋,创作轨迹也是从山岭到海洋。前些年,我写与土地有关的故事,近年来则写与海洋有关的故事,长篇小说《人类世》《经山海》,都体现了这种转变。2021年,我又开始创作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写出10万字之后,山东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王路带着编辑到日照找我,想让我给他们社写一部纪实文学《黄海传》。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决定搁置长篇小说创作,先写这部作品。
他们走后,我想,应该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给我的这个机会,让我能以纪实手法全面地写一写我身边的黄海。于是,我开始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方面,爬梳海量资料,钩沉黄海历史。我将书房里有关海洋的书都找出来,并从网上陆续买来几十本,一起排在我身后的书架上,随手可取,有空就看。
另一方面,沿黄海西岸行走,深入采访。30年来,我曾多次坐飞机飞越黄海,坐轮渡跨过胶州湾和渤海海峡,还从日照坐船去韩国平泽做文化交流,来回都是18个小时的航程。今年我在日照文友山来东的陪同下,在沿途诸多朋友的帮助下,从长江口走到了鸭绿江口。在我看来,这次黄海沿岸行,不只是为了写作所进行的必要采访,更是向黄海致敬的一个仪式。虽然疫情此伏彼起,但我还是瞅准机会,分成两大段得以完成。走在黄海岸边,站在黄海的最南端、最北端以及接近黄海中心的成山头,我觉得自己与传主息息相关,心潮难平。
回来写作时,我恍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老盐工,而且是沿袭古法,煮海为盐。我取来一罐罐一缸缸黄海水,以满腔热情去煮,烟熏火燎,日复一日。终于,我有了收获,最后形成的近30万方块字,就是一个个盐粒子。
我家离海3公里远,在书房的窗口即可看到,我写作累了,就站在窗前望上片刻。全书完稿后,我到海边走了走,看着潮舌一次次舔我的脚趾,突然十分感动。我想,黄海亘久,万古澎湃,而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在短短的生命中,能与黄海结缘,为黄海作传,是我人生一大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