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隐秘而每天挖地不止
――首届凤凰文学奖获奖作品综述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2-04-22
□李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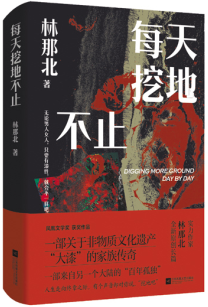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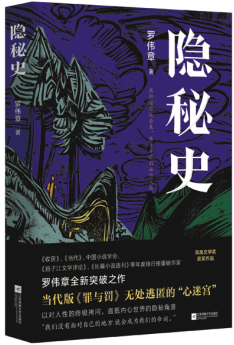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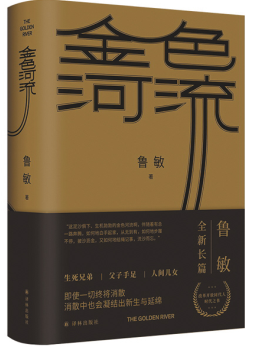

其余三本即将出版
凤凰文学奖是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原创文学大奖,宗旨为“促成好作品,发现好作家,树立好品牌”,在文学出版面临诸多挑战的当下,该奖项对创作、出版和传播全流程都有着一定思考,尤其是对出版机构提前介入作品创作有着较多设计。期待该奖项的持续举办,能够为原创文学的整体发展带来促动,贡献自身的经验。据悉,第二届凤凰文学奖目前已经开始提名工作,计划将于2022年9月公布结果。
首届凤凰文学奖共评选出8部获奖作品,分别为鲁敏的《金色河流》、罗伟章的《隐秘史》、叶弥的《不老》、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郭平的《广陵散》、常芳的《河图》、甫跃辉的《嚼铁屑》、栗鹿的《致电蜃景岛》。
8部作品均为长篇小说,首届凤凰文学奖可以说是一次长篇小说的集中呈现。就写作时间而言,8部作品大部分写于最近两三年,少数起笔于约十年前,将8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可以从中读出当下长篇小说的重要特色。以下分三个方面加以介绍阐述,期待由此可以引起读者对长篇作品阅读的些许兴趣。
集体记忆与个人经验的立体呈现
对记忆梳理与呈现,甚至再发现,是文学的核心要义,8部获奖作品在这一点上,都按照各自的设定努力去做到极致。
鲁敏的《金色河流》写了近40年的现实变迁,主人公穆有衡的人生回望,子一代内心的罪与罚,财富故事后的人性裂变,情爱辩论里的伦理再思,这些纷乱的世相下,鲁敏重点把握的是财富观在过去40余年中的重大变迁,正如她在文学奖颁奖现场所说:“我真的很惊讶,我们已经有了西方发展很多年以后才达到的公益意识,最起码在这一代民企人身上看到了苗头和努力。他们的财富观念快速发展,战胜了我们想象中的非常狭隘的东方财富观。”值得流传的价值必起于民间,有光彩的人格也多挺立在人群之中,《金色河流》在重申,那些在时代巨变中日渐消逝的,正在许多渺小的个体身上苏醒和重建。鲁敏的小说总有一个精神内核,里面藏着人性的隐疾和光亮,亦呼应着那个破败、贫瘠、悲哀、不忍、温暖、良善相混杂的日常景观。当鲁敏把她独特的精神追求与恢宏的改革开放40年相结合时,大时代和小人物之间的激烈碰撞,让人时时想起过往岁月的光荣与梦想。
罗伟章的《隐秘史》是一部在主题阐释和艺术表现上有着重大突破的长篇小说,它是继罗伟章《声音史》《寂静史》之后另一部“发现小说”的创新之作,作品从前两部长篇小说中的乡土心灵史和信仰史抒写中飞升出来,在故事情节的精心构思与艺术技巧的变化中,将人性置于寒光熠熠的刀锋下进行终极拷问,把即将逝去的乡土社会中人性的扭曲放大在现实世界的长镜头聚焦之下显影。就外在形态而言,《隐秘史》以一个扑朔迷离的凶杀案作为追溯人物内心世界的窗口,让主人公桂平昌进入故事叙述的圈套之中,同时开启了人性自我发现的通道,由此小说进入了它的核心,开始深入到人物“隐事实”的书写中,让人性在自我修复和自我确认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
叶弥的长篇小说《不老》,延续了她“以江南写中国”的整体思路,小说以1970年代末的江南小城吴郭市为环境背景,以女工人孔燕妮的婚恋生活为主要情节,展示了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中一群普通人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情状。叶弥无意构建史诗式的宏大叙事,而是以细腻的笔法书写日常的琐屑、人情的纠葛和世事的变迁。这些卑微的生活与大历史形成了互动,并以一种秘密的方式抵达了历史的内在精神。小说主人公孔燕妮等人在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耐心、韧性和热情,寄托了作者对一种理想生活和理想人性的追求: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冷酷无情,但人类的生活川流不息。相信很多年龄50岁上下的读者,可以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看到自己当年的日常生活,或强烈密集,或浅淡悠长,无论哪种都有种置身旧日时光的感受,这大概是文学给人的最大慰藉了。
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更是一部集中精力打捞、辨析、整理历史记忆的长篇,小说紧扣福建沿海这一地域环境和历史背景展开书写,以一个生生不息的家族和一个当下的生存故事,来呈现中华文明在沿海地区得以保存并由此走向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小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为载体,把文明进程中必然遭遇的传承、断裂、坚守、保守、开放、交融等概念,化为普通人的际遇与选择、喜怒与哀乐。千年文明、百年家族和当下生存,多个时间维度下的故事被有机溶解在这部厚重的作品中。
郭平的《广陵散》以古琴为切入点,以平和而优雅的叙述,把作者带入到一个类似古琴曲的深远意境中,其中既有学琴的趣味与艰辛,也有同门的情谊与互助,更有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持续的融合与排斥,并时刻在呈现人与艺术之间关系这一哲学问题――人创造了艺术,无数的人毕生追求艺术,艺术则在人的追求中逐渐呈现出自身的超越性与永恒色彩。小说是迄今为止古琴艺术最为精彩的文学呈现,其中关于古琴的直接论述几乎可以作为“古琴入门”单独存在,而古琴,正是中国文化的标志物之一,承载了太多的民族文化记忆。
常芳的《河图》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小说发生在20世纪初的山东,通过一位革命者和家人在历史漩涡中的际遇、一位巡警局长的家国情仇、一位在济南泺口铁路桥施工的美国工程师的书信与日记等,描摹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人间万象。在历史的碎片中,在偏方、幻术、传说与寓言交互织成的文化记忆中,每个小人物都深陷于生活的困境和信仰的困境,同样是“大时代、小人物”的核心架构,《河图》把众生的命运上升到一个时代的云图,一段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
甫跃辉的《嚼铁屑》是一部“80后”作家走向成熟、开阔、深远、博大的典型之作,作者以人生归宿这一永恒而又充满日常气息与世俗情绪的命题为叙述对象,通过“三部曲”的架构,描述了大量普通人的人生选择,尤其突出了善良、互助等在人世间的力量。小说中穿插了书信、日记、诗歌、独幕剧等多种形式,充满趣味与实验性,同时也对应着生命的丰富多彩。小说实质上是一部当代青年的精神自传和成长总结,故事均发生在新世纪以来的20余年中,对很多读者而言,一切都历历在目。
栗鹿的《致电蜃景岛》是一部年轻作家以更为新颖和感性的笔触所写的家族史,小说有着难以归类的属性,本身充满“回忆”,又充溢着青春、科幻、悬疑等元素。在结构上,更是以相对极端的散点的方式,完成对一个岛上夏夜的叙述,所有涉入者的人生如同折射光线般向新的角度再度折射,照亮某个时刻、某个角落或某张面孔。在现实、回忆和丰富的景观风物共同的建构下,一个关于上海崇明岛大家庭的整体记忆逐步清晰。
在最近关于“元宇宙”的讨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文学作品就是最初状态的元宇宙,是一个跳脱出客观时空规律的平行时空。相信本次8部获奖作品的全部或者部分,会给读者这样的感受。
文学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故事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8部作品自然都是写中国人、中国事,在此基础之上,带有强烈凝练色彩和象征意味的中国元素,也是这一系列作品的重要特色。
首先是《广陵散》,小说始终围绕古琴展开。古琴这一艺术形式已经成功地符号化,往往被冠以“空谷幽兰”“高山流水”等特色。这些意象和境界,也绝非凭空产生,是演奏技艺、精神世界和器物制作三个维度积淀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往往几代人才能出现一个高峰。高峰之外的研习和传统中,古琴同样充满了烟火气息,承载着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作品中多处传达了这样的思想,即超凡入圣的艺术成就来自于长久的坚持和磨砺,来自人本身。“好东西,在我看,都是凡圣并举的。”(第2章)“钟先生的琴,就像《古诗十九首》,不那么漂亮,不那么表演,没有多余的修饰,实实在在,都是人的遭遇。”(第9章)“琴尽管多有归隐萧散之意,但人间情怀却是根本。”(第24章)正是这样雅俗共举,才成就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古琴艺术,连绵不绝。小说也对应当下现实,提出关于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的深思:“古琴,这一曾经陪伴、震动、辉映了几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华民族心灵史的存在,如何滋养今天的人们呢?”(第5章)这种围绕古琴、纵横古今的创作,让《广陵散》的中国元素变得具体生动、温润感人。
《每天挖地不止》同样是一部独具中国特色的长篇巨著,并且在多个“中国元素”上展开叙述。首先,每天挖地不止,语出《愚公移山》里“每天挖山不止”,意在形容一个人对命运的艰难探究。其次是福建沿海这一地域的特殊意味: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福建沿海一方面是北方中原汉族南迁的落脚点和栖息地,福建连绵的群山承载了正统汉文化最后的血脉,并加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福建又是中华儿女南下汪洋、远征海外的出发点,一代代中华儿女超越农耕的局限,在福建启航,把中华文化传播至海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福建为原点的“汉文化圈”。于是,福建既是汉文化的浓缩之地,又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融之处,既充满了中国的气质,又有着浓烈的异域风情。再次,家族的繁衍流传也是高度中国化的,小说以福建一个100多年前的家族和一个当下的个体的故事,来呈现这种文明史上罕见的特点和趣味。最后,贯穿小说的“大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把整部作品的中国特色推向极致。小说包含三个层次的文本,一是改革年代的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状态,即在剧烈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家庭、亲情等所遭受到的冲击以及个人的生存困境,特别是感受强烈的身体的病痛;二是100多年前的家族故事,以传统大漆为线索,与半部近代史高度关联;三是更为久远的历史、更深邃的文化传承,而这一部分文本在第一、第二类文本中时隐时现,本身也意味着传统的无处不在和若有若无,以及今人对它的态度。由此,个人身体的疼痛、家族的伤痕、民族的记忆交错重叠,三者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和人物身上得到了集中的爆发式呈现。三层文本构成了密集的网状结构,故事的纵深感充分延伸的同时,生命的复杂性得到了完美的阐述,一部关于中国的长篇力作也愈发清晰――它甚至可以摆脱创作的具体年份,可以是20年前的作品,也可以是50年后的作品。
除上述两部中国元素鲜明的作品之外,《不老》《河图》《金色河流》三部,都是标准的中国故事。《不老》写1979年的苏州市井和爱情故事,《河图》写辛亥革命前位于济南北部的泺口地区的众生相,《金色河流》则用一位成功企业家牵引出40年改革开放的全貌,三部作品,都在以不同的艺术手法和文本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认识中国。
实力作家的文体突破
每部长篇小说都是一次作家自我突破的机会,在这一普遍的规律之下,首届凤凰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部分作品,异常清晰地呈现出作家在创作具体文本时,对此类作品予以突破的决心和效果。
首先是《隐秘史》,这部普遍获得赞誉的长篇小说在乡土文学的谱系上,具有最新的形式感和意义。此前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一类写的是发生在乡土上的事,乡土、乡村及其中的人是舞台、主角、核心,并且上演着关于人生、命运的大事,充满戏剧性。第二类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进城大潮、城市化背景下,把乡村作为根据地、大本营、来路、精神家园,为城市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影响乃至支撑,包括物资资源、人生经验、处事哲理等,也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某种参照和怀恋。《隐秘史》与上述两类均不同,在这部小说中,乡土已经成为某种遗迹和残留,也不再上演起起落落的人生大戏。这里的乡土,不再有宗族、大家族、村落、大宅等以往的概念,一切都已经土崩瓦解,只剩下极少数因为特殊原因,更多是个人原因、心理因素而留下来的人。乡土,包括它的自然环境、风物、作息规律等等,终于从人声鼎沸的现代化大潮中摆脱出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角。人降格为乡土上的万物之一,而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隐秘史》中的乡土具备了衰败和兴盛两个方面,衰败的是人造之物,最具代表性的是房屋,兴盛的是动植物,是从早到晚的一天、从春到冬的四季,其中的变化和规律变得强大起来。
与乡土的现状对应,《隐秘史》的写法也呈现出全新的乡土小说的风貌。主要特点有两点:一是以博物学的方式呈现乡村,二是以深入内心的方式呈现当下乡村的人。第一种写法让小说充满了文化遗产色彩和自然文学特色,关于方言,关于器物,关于劳动,关于物产,关于自然风物,等等(小说无意中透露出一个秘密,即关于城市的语言在这里似乎是匮乏的)。小说以微观放大的方式,把耕种劳作,把一天的日子、一年的时间等,用近乎考据的程度呈现。第二种写法更切切实实把乡土小说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一个时间相对停滞、与外界近乎隔绝的时空,万物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和乡土成为主角、露出自身的真正面貌一样,人也真正成为人;离开了滚滚奔流的时代,每个人都会以自身的方式成为观察者、记录者和反思者,《隐秘史》也由此获得了独具艺术魅力的“有意味的形式”。
《嚼铁屑》也是一部志在突破成长小说类型的长篇力作。影响一个人成长的因素非常之多,各个要素之间的不同导致了任何两个人的成长都不一致,《嚼铁屑》企图抓住的是成长中的隐秘而普遍的标志性事件,即对死亡的认知。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个对死亡从无知到了解,进而无畏的时刻,这种带有初步哲学思考性质的事件,超越了现实生活,可以算作成长的重大标志。小说共三部分,三个部分的故事全围绕对死亡的接近、认知而展开,彼此独立又相互呼应,最后汇聚为成长的整体问题。
相对于把家族史作为最终写作目标的作品而言,“百年家族史”在《每天挖地不止》中,既是目的之一,更是一种手段和载体,一边承载着此地更为久远的历史,一边承载着当下的生活;一边引发出大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盛和传承,一边也委婉表达了传统技艺和精神陷入了一种破碎、汇聚的关键时刻。依靠整部作品的多重架构和内容的丰富,《每天挖地不止》既可以视为百年家族史写作的最新作品,又在扎实完成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否定”,远远超出了家族史写作的范畴。
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一方面依赖作家的立意与功力,另外也是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确立和清晰。上述所陈述的突破,当是冰山一角,相信把时间线拉长后再看待8部获奖作品,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纯粹的读者,都会有更多的感受和评判。
在沸腾的社会大潮中,长篇小说的写作属于某种隐秘事物,它不会大张旗鼓和万众瞩目,也不能这样。长篇小说的真正法宝,无论是创作层面还是阅读层面,是一种信念和梦想促动下的“每天挖地不止”。文学奖的评选只是围绕一部作品工作的开始,真正的阅读与传播、感受与阐述,都在文学奖之后。
对长篇作品的完整阅读应该是必要和长期的。正如雷蒙德・钱德勒所说:“一个男人,每年至少要大醉两次,这是个原则。”大醉是一种极端体验,断片、忘我、沉浸、心潮澎湃等,深度阅读也是如此。一个当代社会的读者,每年至少要读两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这也应当是一个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