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生命在美善之光里上升
――李东华“致成长・焰火”系列三人谈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1-09-10
关于作品:曹文轩、朱永新――
东华作为作家,一路向高的行进轨迹预示我们:她的好作品还在后头。东华写出的作品,对美善、责任与温情的执着守护,是在传达着成长必须的底色。
东华的写作,烙有鲜明的“东华”家印与族徽
东华的写作一直十分认真,她对她的书写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每部作品出版后之所以都受到一致的赞扬,就是因为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她苦心经营之后的艺术结晶。作为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她,大概早看清了一点:世上的书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品,一种是产品。她要写的是作品。作品要做到每一部都是独特的,每一部都有可以经得起丰富解读的空间。它们出自她之手,是一个家族的成员,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是可以被指认的。但它们又是各自不同的,不同的意蕴,不同的构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展开方式,不同的心绪缭绕,每一部都是“这一部”。《焰火》《小满》《星芒》等,无疑烙有鲜明的“东华”家印与族徽,但它们有一部与另一部“似曾相识”吗?没有。它们是它们自己,各自傲立在自己的风景中。
这些作品产生在一个注重产品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辽阔而丰饶的市场吸引了众多作家的目光――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凶猛消费,使很多作家将注意力放在了人头攒动的消费者的钱袋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作品上。如果说,东华处心积虑琢磨的是如何将一部作品按“艺术品”去书写的话,那么这些写作者琢磨的则是如何让那些消费者主动地、忙不迭地将钱从囊中掏出。于是,写作者的注意力完全变了:不再寝食不安地去构思一部无论从语言还是题旨、人物还是故事都很地道的作品,而是昼夜不停地揣摩消费者的心理――尤其是卑下心理,然后竭力迎合他们的心理。一本本络绎不绝地出版,也许书名不一样,但无可回避地重复、克隆却分明就在。它们无论怎样乔装打扮,明眼人还是会轻而易举地看到它们是从同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不是作品,而是产品。
这样一个对销售排行榜顶礼膜拜的时代,东华却能坚守她从创作开始的那一天就认定的路线和方向孤独而安静地走她的路。她对自己是有规范的,同时又是自由的――她对自由的理解就是让作品成为她想要的样子,好看的样子,可以让人欣赏的样子。她只想让她的作品活得长久些,更长久些。
在一个轻佻、浮华,将乐趣视为最基本的阅读需求,而毫不在乎作品从此沦于浅薄的时代,东华却是一个追求庄严和作品深度的作家。她考虑的问题都是一些十分严肃的问题。民族国家、成长之痛、灵魂与人之本性,这些问题好像并不属于儿童文学。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自从对“成长小说”有了命名和对它的合法性进行了周密的论证之后,昔日的儿童文学版图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的疆域似乎于瞬间被大大地扩展了,在儿童文学名下,有了另一种形态的文学,它们在许多方面一样需要遵循儿童文学的一些规则,比如对性和暴力的规避,但它也有了从前的“标准儿童文学”不能给予的自由,尺度变宽了。一些思想面较宽且又深邃的作家感觉到,更深度的思考有了一路通达的天地,那些在“标准儿童文学”那里很难进行的思考,现在变得酣畅淋漓了。
这个领域似乎很适合东华这样的作家,因为她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环境与一般作家不太一样。她要思考更多更深入的问题。但这样的写作,依然主要是面对孩子的,因此她的思考依然是要有所制约的。她清清楚楚地懂得,所谓的深度在哪儿。在人性――对人性的探究与追问。可是她不能像耶利内克和帕慕克那样毫无顾忌地写人性――人性之恶,人性黑暗深处的恶。东华找到了最恰当的进入深度的途径:写人性的微妙。
其实,传统的成人文学,特别是古典形态的成人文学,也并没有因为追求深度而一味去写人性之恶,它们寻思和书写的也是人性的微妙。比如《红楼梦》和《围城》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深度获得并不在对极端人性的极端描写上,而只是在“微妙”二字上。从现在来看,也许这样的作品更加可靠,它们所具有的深度才是经得起思索的深度。东华是一个有文学史背景的写作者,她选择了微妙――对人性微妙之处的凝视和执着的剖析。写到《焰火》,她让我们更加透彻地领略到了微妙的人性。哈娜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哈娜站在了我们面前。就如同一道堤坝横腰拦断河水。醒目而突兀。”从此“我”的心不得片刻安宁。为什么却是无法言说的?因为微妙是很难被言说的。孩子与孩子的关系、老师与孩子的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都很微妙。但却分明是存在的真实状态。东华对微妙的选择,既使得她的文字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孩子面前呈现,又使得她的深度追求得以完美实现。其实,对人性微妙之处的描写比那种极端化的人性描写更见对人性的洞察力,也更耐人寻味。
“不错。哈娜来的时候校园里八仙花正开始凋落。从4月到8月,就算暑假两个月学校里没什么人,在漫长而寂寞的花期里,八仙花也一直尽职尽责地明媚着。那一天,我望着它的花瓣露出的颓败的底子,被雨水浸泡过,像揉皱的手纸一样。脏污。憔悴。我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向它――怒气冲冲,指责的,厌恶的。”读这样富有节奏感的文字,我想到了一个词:语流。
东华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可小觑。那些字和词,经过她组织而成的句子,面孔新颖,自成一体。还是那些字,还是那些词,但经她一番调动和安排之后,有了出人意料的魅力。她指挥字词,十分自如,修辞得心应手,比喻不落窠臼。那些字词犹如满山的羊,她挥起鞭子轻轻一摇,羊群如云如潮,让整个山生动了起来。长句短句恰到好处的搭配,制造了一种叙述的节奏,也有缓缓流淌,但在总体上是一往无前。其间,没有滞涩,没有半星拖沓和迷瞪,阅读总有顺流而下、有清风从耳畔掠过的快意。就在这不由自主的“随波逐流”之中,意境有了,诗性有了,人物有了,精神有了,该有的都有了。
东华以她一路向高的行进轨迹预示我们:她的好作品还在后头。
东华的作品,有着故事的特殊气味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女性作家的书写似乎更善于在表达微妙而纠结的莫名情绪上,在细腻而痛苦的莫名的心理变幻上。她们更喜欢讨论的问题通常是情感问题。也许是女性心理的特殊性,她们喜欢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让文字呈漫漶式的无方向流淌。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似乎不是走在一条实实在在的路上,而是漂浮在没有边际的水面上。那是一种特别的阅读体验。
东华的作品呢?除了以上说的这些特质(我以为《小满》这样的作品,只有东华才能写出来),还有一个特别出色之处,而这“特出”之处,通常似乎是属于男性作家的专长,这就是编织故事。我们笼统说:什么叫“男性作家”,男性作家就是一些说故事的人。我以为这么说,大概没有什么疑问。而如果说:什么是“女性作家”,女性作家就是一些说故事的人。这么说,似乎总感到这个判断有点不自然。而东华呢?她以她的长篇和短篇告诉我们,她就是一个很在意说故事又很善于编故事的人。《焰火》《小满》以及收在《星芒》中的8个短篇,都向我们讲了很别致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是东华向我们第一次说。其实,在文学作品中,那种新鲜的故事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大多数故事都属于重说。我很喜欢《星芒》中那8个短篇。你从那8篇作品的名字就能感受到这些故事的新颖了。
关于故事的问题,我更想说的是东华的故事的特殊气味。我们都在说故事,可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被我们经常谈论的大家,他们所讲的故事都各有特色。紫式部的故事、曹雪芹的故事、茨威格的故事、契诃夫的故事、海明威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川端康成的故事、沈从文和鲁迅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故事。我以为,故事是有气味的,不一样的气味。看东华的作品,我感受到了这一点。
东华故事的气味,可能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女性的眼光和心态,比如对世界的永远善意,比如脉脉温情,比如骨子里的诗意,等等。
东华的功底,是建立在基本功之上的
东华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有关文学的理念和知识,还是比较古典的。当然,她后来被现代性的文学理念和知识所包围了。但包围归包围,那些古典的理念和知识已经深入骨髓,融化在血液之中了。那么古典的理念知识究竟教导了她什么呢?教导了她有关文学的基本功。这些基本功在古典作家那里传承了一代又一代。那些理念和知识也许并不多,但那是无数作家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文学创作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也非常管事,比如如何实现主题――小说不能主题外露(契诃夫关于盗马贼的论述),比如人物描写(肖像描写、衣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比如细节描写,比如倒叙、插叙、顺叙等,你只要掌握了它们,你的作品就有了。遗憾的是,这些写小说的基本,现在不讲了。因此,未来的小说创作总有点让人担忧。
我们在东华的小说里,恰恰看到了这“老一套”。殊不知,这老一套是写作的基本方法,是基本功。东华作品的建构,离不开这些基本。她作品的成功告诉我们,基本方法、基本功有多么重要。我们不要轻视古老的话题。也许,正是这些古老话题才是真正的话题。东华仗着这一切,成全了她的故事,成全了她的人物。比如细节描写――她深知细节描写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总能在她的作品中永远地记住了一些细节。《小满》中,那个“绝缘体”的男生在网上约小满去咖啡馆,小满很纠结:去还是不去?小满手握一朵珍珠般的小白菊,开始扯上面的花瓣,一片说“去”,再一片说“不去”,就这样轮番说着,而扯到最后一片花瓣时,正好轮到说“去”。我想,这个细节将是我永恒的记忆。
最近一年多时间里,我在讲写作时,更多地给他们讲这些写作的基本方法。我之所以如此,是我看到了当下写作的危机。以后,我再讲这些基本方法时,我会拿东华的作品举例。
是真正的既有儿童又有文学的儿童文学
李东华的《小满》是一本以平常生活为背景,关于爱与责任、善与温情的成长小说。是完美兼顾儿童生活和文学精彩的佳作。
小满,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的名字,也是故事的主人公。生活中的她在中考超常发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重点高中。而她的好朋友邱冰轮却意外地名落孙山。为了筹集学费,小满在暑假去肯德基打工,遇上了自己的同班同学,发现好朋友的男友已经弃她而去。自己的家庭也节外生枝,父亲失业,奶奶与妈妈爆发家庭“战争”而回到老家。小满一边心系朋友,为朋友担忧;一边又牵挂奶奶,回到老家照顾奶奶。没有想到,在这里意外遇见了一直心仪邱冰轮的富家子弟汪诗帆。围绕坟地的搬迁,揭开了奶奶和汪诗帆身世的谜底,奶奶青春时刻骨铭心的爱和汪诗帆母亲的“寄生”生活,让她见证了社会的世态炎凉,也终于勇敢地走出了内心的惆怅自卑,管住了自己心中的那条“小蛇”,接受了那个虽不完美,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
好的儿童文学,它会让儿童看见自己,让成年人看到人性
应该说,这本《小满》写出了当代少年的挣扎、困惑与蜕变、成长,写出了以小满为代表的少年一代,在“一团乱麻、混沌的生活中对美善、责任与温情的执着守护”。东华在创作手记中写道:每一个孩子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青春期所特有的纯粹、饱满、梦幻般的思绪,总是有着因为智力、家境、外貌等个体间与生俱来的不同,所带来的或明或暗的底色,“由此所产生的诸如自卑、迷惘、傲慢、挫败……成为成长路上必然要躺过的泥泞,这就是女孩小满要面对的现实人生。”我想,这也是所有青少年要面对的人生。好的儿童文学,不仅让儿童如痴如醉,也让成年人爱不释手。因为,它会让儿童看见自己,让成年人看到人性。
关于创作:李东华――
在我提笔想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本能的是觉得我该做点什么,我也很清楚我想写些什么。
在焰火里,善与美写得毫不犹豫
在《焰火》里,我写哈娜的善与美写得毫不犹豫,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曾在我的生命里真实地存在过,更因为随着时光流转,几十年过去了,这美与善依旧与我的内心相伴而行,让我确信,青春年少时一个女孩子瞬间绽放的光,如焰火般短暂,却真的拥有照亮别人一生的力量。每一个孩子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青春期所特有的纯粹、饱满、梦幻般的思绪,总是有着因为智力、家境、外貌等个体间与生俱来的不同所带来的或明或暗的底色,由此所产生的诸如自卑、迷惘、傲慢、挫败……成为成长路上必然要�过的泥泞,这就是女孩小满要面对的现实人生。
于小满中,看见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
小满愿意倾听别人的故事,也愿意倾听自己的内心。当她沿着故事的藤蔓慢慢进入他人的世界,那些看上去平凡的、沉默的甚至有些刁蛮的各种难以理解的人,原来都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精彩。她用自己的倔强与善意默默缝合着成人世界的罅隙,悄悄抚慰着朋友的伤痕,坦然接受不完美的自我――有缺憾没什么大不了,你就是你,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就像漫山遍野的小菊花,过去小满总是叫它的洋名“玛格丽特”,现在她叫它的土名“木茼蒿”,然而无论你叫它什么,花朵只是我行我素地摇曳着自己的色彩。
在星芒之间,获得勇气和力量的支点
在这部短篇集子里,那个爱读书的小女孩千灯,那个残疾小男孩韩星芒,他们的故事都是有原型的。这缘于2017年的冬天,我到湖南、山东一些农村里去调研乡村孩子的阅读情况。乡村孩子在读书、学习上,多半不像城市孩子有父母在旁边督促得那么紧。他们大多是父母外出打工,由爷爷奶奶照看的留守儿童,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阅读的热望,我还记得初见千灯和她的小伙伴们时,他们正用流利的、清脆的普通话朗诵着一本童谣。千灯有一双美丽的清澈的大眼睛,无论问她什么,她都是落落方方,对答如流。
在我提笔想写下这些孩子们的故事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该做点什么,以点燃和保护他们阅读的热情,让他们获得一个能够撬动命运的支点。可等我写完了,回头再去看这些文字,我却觉得是他们给了我一个获得勇气和力量的支点,是他们的光芒照亮了我的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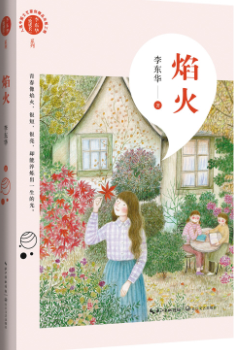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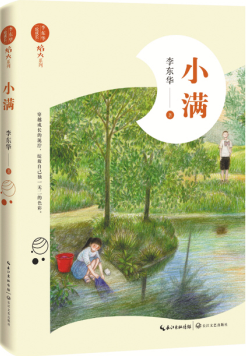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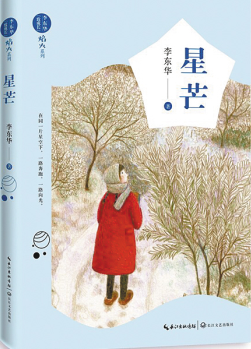
李东华“致成长・焰火”系列,包含《焰火》《小满》《星芒》三本,是作家李东华全新的创作、内容各自独立但主题相关的成长励志小说,观照当代青少年在青春期所面临的人性困扰和生命难题。该系列兼具温暖和硬度,直面新时代、解读新成长、导引新少年、塑造时代新人品格形象,审视青春、昭示成年,彰显“写实性儿童文学的意义”。文字低回华美,叙事不落窠臼,不同的视角和声音交织而成对青春的立体勘探,对成长的冷峻叩问,对美善的执着守护。
该系列目前已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陈伯吹国际儿童图书奖、文津图书奖,入选“中国好书”、中国版协30本好书、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等。

曹文轩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作家)

朱永新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家)

李东华 (“致成长・焰火”系列作者、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作家、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