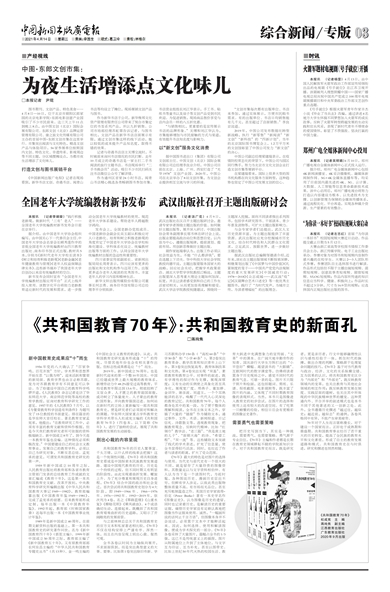-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共和国教育70年》:共和国教育史的新面孔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1-04-14
□蒋纯焦

《共和国教育70年》
杜成宪 主 编
蒋纯焦 副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20年9月出版
新中国教育史成果应“十”而生
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学术界和思想界开始反思“以俄为师”,迎来活跃和繁荣的新局面。教育学界也由言必称苏联,变为对苏联教育学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为了给建设中国自己的教育科学鸣锣开道,《人民教育》杂志记者走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的教育学教授,征询对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1957年的《人民教育》7月号,以《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为题刊发了15位教授的书面意见。排在篇首的是华东师大首任校长、著名教育史家孟宪承,他提出:“在教育研究工作中,必须有丰富的教育文献和资料作根据,但是今天我们教育研究者所可依据的资料极端缺乏。新中国成立8年了,到今天连一本教育年鉴也没编。这种情况必须积极改变。”中国要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自己的教育学科,必须以自己为研究对象,不断反思总结。孟宪承的意见,可谓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一声。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人民教育出版社将教育部和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发表的总结教育工作成就的文章汇编成《教育十年》,这是第一本共和国教育史文献。改革开放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部编纂出版《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完成了孟宪承的宿愿。后来教育部形成定制,每年出版一本《中国教育年鉴》。1992年起,教育部(时称国家教委)还每年出版一本《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
1989年是新中国成立40周年,在前期文献资料出版的基础上,第一本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著作问世,名为《新中国教育四十年》(郭笙主编)。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教育部主编了《新中国教育五十年》,又有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共13种)、金一鸣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从此,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基本形成逢“十”的传统,尽管其他年份也会有相关著作出版,但标志性成果都是应“十”而生。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新时代迎来的第一个整10年国庆。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新增劳动力中48.2%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彻底扭转了文盲众多、人才匮乏的教育弱国面貌,成功树立了体量庞大、人才辈出的教育大国形象,并向教育强国迈进。如何站在新时代的立场上重新编写一部共和国教育史,便是研究者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华东师大国家重点学科教育史学科学术带头人杜成宪主编的《共和国教育70年》(四卷本,以下简称《70年》),进行了独特的尝试,展现了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生动画卷。
别出心裁的内容呈现
共和国教育70年的历史人繁事富、千头万绪,以什么样的线索去把握?这是一个统领性问题。《70年》将共和国教育史看成是中国探索本民族教育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不同时期又有明显的阶段性,由此实现着曲折发展、螺旋上升。为了充分尊重和展现历史自身进程,《70年》结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迁,首次尝试将共和国教育史划分为4大阶段,即1949―1966年、1966―1976年、1976―1992年、1992―2019年,依次列为4卷,名之《筚路蓝缕》《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乘风破浪》。4个成语确切生动,连接起来,既概括了共和国教育艰难曲折的历史道路,又昭示了开阔敞亮的发展前景。
与之前林林总总关于共和国教育史的官方文本和私家著述相比较,《70年》不仅在结构安排上严谨有序、浑然一体,而且在内容呈现上别出心裁、粲然可观。
全书各卷以时间为主轴纵向展开,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典型意义的大事、要事。比如第1卷突出除旧布新、学习苏联和办学150条(“高校60条”“中学50条”和“小学40条”),第2卷突出教育革命、教学改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3卷突出恢复高考、教育体制改革和文化热,第4卷突出实现“双基”、素质教育和教育公平。对事件的叙述,既有学理性的探讨作为支撑,展现深厚度;又有生动的实例使之具象化甚至具身化,展现宽广度。邢燕子、董加耕、金训华、谢彦波、刘道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唤醒了一代代人心灵深处的教育记忆。共和国教育70年,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某一段,为了便于整体的理解和阅读,全书在主体文本之外,穿插了大量的“链接”作为辅助文本,通过事件、文件、术语、新闻报道、日记信札、诗歌散文等,透视教育现象、把握教育观念、反映时代精神。比如“红领巾”教学法、“老三篇”、“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面朝大海”的诗、“希望工程”、“双一流”等。这些辅助文本突破了线式的学术表述,扩充了信息量,使全书显得轻巧活泼。同时,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扩大了受众范围。
《70年》最大的特色是对图片的选择与使用。当代史与前代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其数量足以与文字资料相伯仲。有人认为当下是一个读图时代,为赶时髦,各种图说历史、漫画历史层出不穷,但鲜有学人涉足,以致此类出版物整体质量不高,有市场而无品位,甚至充斥粗制滥造之作。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有一本史学名作《图像证史》,认为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着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痛惜历史学家没有足够认真地把图像当作证据来使用。诚然,“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但图像本身并不会说话,必须置于文本中才能鲜活起来。因此,如何选择、使用和解读图像,便成为学术探究的一部分。《70年》各卷采择了大量图片,篇幅占全书的1/3强,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插图,图片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体地位,与文字互为印证、互为补充,甚至以图带史。比如上世纪50年代火热的校园生活、教育大跃进中充满想象力的宣传画、“文革”中的课本、在广阔天地辛勤劳作的知青、国庆游行大学生方阵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渴望读书的“大眼睛”、互联网时代的数字课堂等,仿佛将读者置身于历史现场之中,感觉不同时代的教育气息。可堪一表的是,图片不只限于照片和绘画,还包括题词、剪纸、乐谱、报纸截图、电影剧照等,既丰富了图片的内涵,又体现了不同时期教育图像的表现样式。当然,本书只是图像进入教育史的初步尝试,在图片的选择和使用上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有了吃第一只螃蟹的经验,相信日后会有更精彩的图像证史著作。
需要勇气也需要策略
把历史写到当下,其实是一种挑战,需要勇气,也需要策略。勇气源于专业自信,《70年》主编和作者都是长期在教育史领域耕耘不辍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对于共和国教育史而言,既是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行文中能够融理性认识与感性经验于一体,抓住时代的脉搏,做出合理的判断。策略源于处理复杂问题的技巧,《70年》基于对当代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纵横交错、互为因果的认识,将共和国教育史区分为“内部史”和“外部史”,既反映教育领域内的变革,也关注教育与其他社会领域的相互作用;既反映教育发展在制度、实践层面的建树,也关注其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嬗变。这种贯通内外、开合并举的叙述模式也是本书不同于其他著述的又一创新之处。此外,全书遵循历史撰述“越过往,越似史;越近前,越似志”的通例,各卷风格同中有异,不致产生审美疲劳。
70年对于人生而言堪称漫长,对于建设一个国家而言,正好处于成熟期和鼎盛期。共和国教育事业经历了若干重大的历史转变,提高了全民族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形成了自主的教育发展道路和模式。共和国教育史在与时俱进,研究和撰述也悄然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