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新时代民间文化的创生与绵延
——简评王勇英长篇小说新作《我们家》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4-1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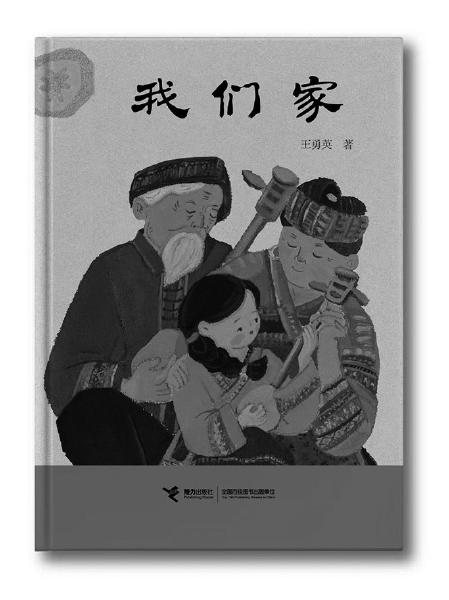
新时代以来,作为原创儿童文学一翼,地域儿童文学创作春华秋实、生机勃勃。这其中,广西本土作家王勇英依托西南地区壮、苗、瑶、布依等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小说创作,将山林物产、乡风民俗、民族艺术与童年生活融为一体,在呈现风情独具的大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为新时代地域童年表达提供了诸多成功范例。相较《巴澎的城》《弄泥木瓦》《水边的孩子》等客家文化童年书写之朴实,与《里湖山钓蜂》《泥骨布朵》《少年陀螺王》等瑶族、苗族乡土童年故事之灵动,王勇英在长篇小说新作《我们家》中淡化“童年”生活,将“文化”置于审美核心位置,通过一系列富有历史纵深感的情节铺排,使整部作品显示出卓尔不凡的文学气象。
作品聚焦广西花山地区一个多民族家庭的生活日常,在生动描述少数民族地区普通家庭幸福生活的同时,不仅真实再现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而且形象展示出新时代民间文化的代际传承与守正创新。小说字里行间隐逸着普通家庭的幸福密码,表征着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化的多重现实、多维趋向。
其一,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创生与转化。
小说涉及的民间文化品类繁多:叮、鼎、漂竿、壮锦、苗绣、岩画,等等。这些民间文化大都有悠久历史和特殊功能,比如,传说中的叮,在很久很久以前是歌师的法器,歌师用叮来跟灵魂说话;传说中的鼎,在古时候用来把唱天婆的话传给自然万物听,也唱给自然万物的灵魂听。而无论歌师弹叮唱咒歌,还是唱天婆漂竿弹鼎,跟山林、花木、风雨、阳光、江河说话,都既是对逝者的缅怀与告慰,也是与大自然的交流,对天地万物的感恩。足见,这些文化实物、实景所表达的,不仅是壮、苗等少数民族经久流传的生活方式,更是这些民族一脉相承的生活信仰与价值观念。
也正因如此,当小孙女嘎花在老祖母花婆影响下无师自通学会漂竿弹鼎;当古老的叮被改造成天琴,并将进入学校课程,成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一部分;以及当壮锦、苗绣等民间服饰文化技能被引入课堂,在各民族孩子手中焕发生机的时候,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现实创生与代际绵延就成为生活主调、文化方向。
其二,社会发展对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浸淫和改变。
《我们家》的核心内容是老叮公一家三代人的幸福生活。故事里,祖父辈的叮公和花婆是壮族、苗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人。叮公竹排漂江、抱叮弹唱的场景,花婆踩竿漂流、弹鼎唱天的画面,无疑是壮族、苗族源远流长的民间习俗的一部分。而作为父辈的杨长平、杨远安和爱侬则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与融合。杨长平将叮改造为天琴,并最终成为专业制琴人;杨远安夫妇以知识反哺家乡,他们的眼界、学识直接推动着家乡的教育发展、文化更新。至于爱侬,则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参与者、践行者。依托开阔的视野、前瞻的观念、卓越的才干,借助广泛的人脉、丰富的信息和便捷的新媒体手段,爱侬消弭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少数民族山村的封闭、落后。她以时下最为流行、高效的直播带货,不仅帮助很多乡亲致富,还彻底改变了自己和整个家庭的亲情模式、生活面貌。而鼓嘎、嘎花作为大家庭的第三代,其精神风貌、价值选择不仅表征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绵延、再生,而且还显示出文化的新异、多样所给予年青一代的广阔空间与无限可能。故事中,鼓嘎的自尊独立、吃苦耐劳,嘎花的聪明伶俐、敢想敢做……无不喻示着大家庭和谐、幸福的未来。
其三,多元文化互动中个体形象的重构和塑型。
小说通过大量场景、细节渲染了多元文化互动中“我们家”三代人相亲相爱的亲情模式。这其中既隐含着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幸福密码,也彰显着包括传统习俗、民间艺术、信息文化、现代观念在内的多元文化互动所给予乡村个体生命的巨大推力。实际上,也正是这种力量助力“我们家”与时俱进,不断由农耕生活向农商学复合型家庭转型;也正是这种力量,牵引着家庭成员尊老爱幼、彼此关照、相互支持,在缔造和谐、美满幸福生活的同时,也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故事里,90岁的大家长老叮公专断而固执。他一方面兴致勃勃悦纳由手机、网络、煤气灶、冰箱、汽车等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执守“江上行排,弹叮唱咒歌”等古老乡俗,也拒不接受别人把“叮”叫作“天琴”。甚至为此迫使长孙鼓嘎离家出走,一去不归。小说末尾,老叮公看视频直播时,十分牵挂山中采风的孙儿鼓嘎,这不仅代表着祖孙俩的和解,更预示着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代际文化冲突的最终弥合。
通观全文,不难发现,作家浓墨重彩塑造老叮公形象颇有些意味深长:生活如同浩荡的江流滚滚向前,连90岁的老叮公都在新时代多元文化的互动、交汇中逐渐跟上了生活的节奏,更何况人生盛年的父辈和朝气蓬勃的鼓嘎、嘎花、二弦们?事实也是如此。小说里,除了老叮公,另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是爱侬。身世特殊的爱侬是这个家庭的“异类”。她上过大学,本来已在大城市成家立业。婚姻失败后,她回到家乡散心、疗伤,却不经意间发现了生活的另一种样貌、可能,由此开始了全方位的人生转型……与爱侬不同,大哥杨长平、长嫂田绣花经历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生活锻造、文化塑型。限于篇幅,这里不做阐释。
总之,小说中,多元文化互动不只是构建“我们家”幸福生活的核心要素,也是每个家庭成员参与生活、感知幸福、创造未来的主要依托。
其四,民间文化之于童年成长的牵引和滋育。
诚如前文所述,与王勇英“乡土童年”系列其他作品不同,《我们家》中,儿童不是故事主角,童年成长也并非小说主线、情节核心,而是仅作为家庭生活参与者、家庭文化建设者、家庭幸福见证者出现。这一方面是“我们家”的创作定位所致(三代同堂家庭往往“长者为尊”,孩子通常并非家庭核心);另一方面,这也是生活“完整性”的体现——儿童和童年固然重要,但也只是社会文化的基本构件,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其生命成长、生活动态仅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基于此,“我们家”的生活图谱中,鼓嘎、嘎花、二弦等孩子对家庭生活的参与、民俗文化的传承固然不是核心、焦点,但也必不可少。毕竟孩子代表着民族的希望、家庭的未来。无论文化传承、发展,还是家庭和谐、美满,都少不了孩子积极、主动的参与,热忱、聪慧的贡献。小说中,嘎花就是如此——率真、单纯、好奇、热忱、聪颖、能干。适逢假期,家庭生活的每个场景都活跃着她的身影:调节画家时风与祖父之间的尴尬气氛;随祖母花婆水上漂竿弹鼎;去医院照看受伤的爸爸……彼时,小姑娘既是大家庭的开心果、润滑剂,也是家庭幸福的参与者、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末尾,无论是鼓嘎的民间文化采风,还是嘎花的家庭责任承担,无不体现了少数民族年青一代的主体意识与创造精神。
内容主题之外,《我们家》在形式表达层面也颇具特色。小说以画家时风采风、作画为线索,通过时风入住嘎花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层层推进、抽丝剥茧般渐次呈现出这个三代同堂多民族大家庭的生活风貌。小说细节生动、语言鲜活,情节起承转合间悬念频出,读来颇为引人。
综上,《我们家》通过一个少数民族大家庭的生活图谱勾画出广西花山地区民间文化的发展脉络、传承轨迹,并由此浓缩且折射出时代变迁中普通家庭、普通人的文化参与、文化创造。小说中,作家写的固然是广西花山地区一个普通多民族家庭,但这个“小家庭”所映现的却是多民族融合、国泰民安的“大家庭”幸福生活图景。
基于此,就题旨内涵和价值取向而论,《我们家》已非单纯的儿童文学作品,而是融民间文化传承、家庭文化创生与童年成长表达为一炉的社会文化小说。也由此,《我们家》的出版某种程度上不仅预示着王勇英小说创作的新趋向,而且也表征着她“乡土童年”文化表达的新高度、新成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