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全屏阅读
- 放大
- 缩小
- 默认
草原覆盖着语言的光芒(二)
——鲍尔吉·原野、汪政对谈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3-0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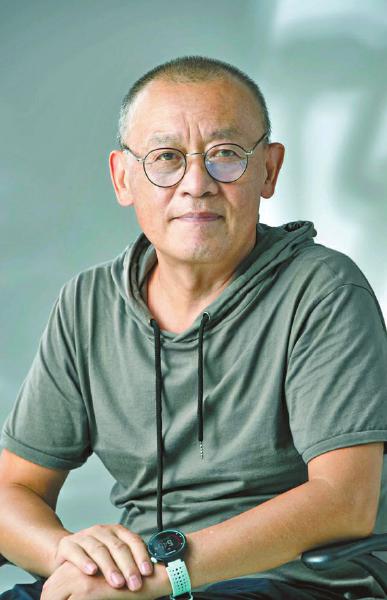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
汪政:原野老师,你以前有过写诗的经历吗?
鲍尔吉·原野:我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写诗,很早以前我被别人称作诗人,我跟赵健雄、邹静之、林莽是写诗认识的。
汪政:出版过诗集吗?鲍尔吉·原野:没出过诗集,后来有机会出,我没出,我觉得我的诗写得不好。
汪政: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说到你的散文,说到你的语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在自觉地,或者自然地营造一个富于诗意的世界。
鲍尔吉·原野:我一直喜欢读诗。中国的诗歌,我长期读杜甫,读了10多年,把好几本杜诗选本读烂了,又买新的。外国诗歌也读过一些。现在微信里读诗很方便。昨天早晨,我读了瑞典诗人索德格朗的诗:“当夜色降临,我站在台阶上倾听;星星蜂拥在花园里,而我站在黑暗中。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读过这首诗,我觉得一天都会愉快。我把诗歌当作营养,当成蛋白质和纤维素。
汪政:一般来说,作家对语言的贡献都可以掰开了、揉碎了来讲。一个作家对语言有所贡献,其实就是他建构了个性化的语言风格、语言世界。再进一步,就是这种语言能够成为一种风尚乃至一种标准,人们会去学习它、模仿它、使用它。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标准。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若干年后能够留下来的,就是我们依然能够使用他的语言和话语的风格。
你的创作为文学语言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语言建设就是要创新,要对语言重新发现,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起死回生,从而丰富语言的功能。比如,在言说的惯性里,“躺”这个词说的肯定是人或者动物。现在你说“草不躺着”,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认识到“躺”还可以有新的用法。再比如,对内地读者来说,什么是“辽阔”?什么叫“辽”?什么叫“阔”?这在他们的脑海里可能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你的草原写作让人们对这些词,这些字有了实在的理解。你的写作,整体上让我们重新发现了许多词,并经由这些词重新认识甚至重新发现了世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草原写作具有“异质性”,它不仅在文化上,也在语言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许多习以为常的、已经固化的事物和经验。不妨再说“辽阔”,“辽阔”是什么?你写辽阔,并不是采用词典的讲法。你的辽阔是实景的、感官的,通过写作,你带我们认识了草原,又因草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辽阔”。
在你的作品中,读者会知道草原,还会知道“草”,并通过草体验到色彩的丰富。草不是单一的绿色,它五光十色,早上、中午的时候都不一样,春天、夏天、秋天也不一样。它就像在不同时节生长、成熟的庄稼一样,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季节的轮换。如果你没有写,或者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对于草原、草、颜色等等词的认识就固化了。
另外,你的语法有些特别。我是语文老师,我看到你作品中有些词不在按照语法应该在的位置上,你悄悄地给它挪了窝,一下让我们对这些字词和句子有了奇妙的感觉。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自觉地、有心地在语言上用功的作家。你在这几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当然,有些东西是语言的天分,语言的感觉,并不是刻意这样写,它就淌出来了。蒙古语的语法可能跟汉语不一样,可能悄悄地改变了你对汉语词的排列,你觉得那样写很自然。但对我们来讲有一点陌生。
语言的建设就是这样。第一是造出一些新词,像普希金、但丁,还有中国的鲁迅曾经那样做的,包括从其他语种翻译过来的,都可以产生新词。第二是重新激活,腾挪踢打,赋予旧词新的含义。第三是通过写作重新认识一些词,使它回到原初。在你看来,我们说的草原不是草原,我们说的草不是草,你将这些词返回到了事物的本真。第四是语法的变化,语法稍微变化一点,语感、调子就不一样了。我特别想听听你在平常怎么琢磨这些事。
鲍尔吉·原野:您总结得好。您刚才说的关于语言的几个方面,我有的做过努力,有的并没有达到,但是我觉得能这样做的话,就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作家需要警惕语言被固化,思维被固化。世界既然多了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应该和别人不一样,又要区别于其他作家,而不是彼此相仿。一个作家应该有这样的自觉。
有些词在我看来是死的,麻袋里边是干瘪的,上面写俩字,“草原”。实际上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草原,只不过认识这俩字,说到草也是这样。我觉得我的任务是,半夜把这些麻袋打开,在里边装上东西,让它鼓起来。我作品中字词麻袋里边是有东西的,你解开它,能看到茂盛的草原,里边甚至有河流。
写散文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写散文离不开日常生活,你一定会写到风,写春天,写月亮,写河流,写小孩子,写老人,这些事无数人都写过了,你还写什么?你没有立锥之地,过去说“脚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散文家的处境。除非你在语言上有更新与复苏。草原的含义是你自己说的,跟屠格涅夫、契诃夫说的都不一样。你写的月亮也跟别人不一样。
汪政:你说月亮是退着走的。鲍尔吉·原野:我觉得月亮确实在退着走。把世间所有事物重新说一遍,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最重要的不是说得很独特,而是说得美,大家读了都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风格化的问题,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我们谈论的话题有点接近语言哲学,像乔姆斯基或者维特根斯坦所研究的领域。席慕蓉老师对我说:“原野,我们对自己还是有所期许的。”她说的有意味,她不说雄心壮志,不说野心,不说以后要当大作家。她说我们要对自己有所期许。我也觉得要对自己有所期许,期许我的语言还能更好一点,像福克纳所说,“我希望我写得比我以前能好一点”。比以前好一点,这个目标永无止境。
我尤其愿意跟牧民们学习语言,他们用蒙古语谈论马,相互打趣,赞颂祖先和山川河流,一语多关,鲜活生动,妙不可言。
汪政:你把语言稍微动一下,减一点东西,加一点东西,就与惯性的语言有了区别。这3本书打开来,任何一页都有这样的语言现象。比如,“盎嘎骑着这匹枣红马,奔向草场”。这是我们说的话,你呢,前面也没交代,后面也没着落,你在草场前面加俩字“西边”,真的就不一样了。“西边”在你那里很重要,是吗?
鲍尔吉·原野:我固执地认为,盎嘎不能骑着枣红马奔向“草场”,世上不存在“草场”。它要么在西边,要么在东边,要么在北边。我认为这么写不是啰唆,是准确。
汪政:这里面还有一种草原生活的经验和蒙古语的经验,我猜测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很感性的,对不对?
鲍尔吉·原野:我掌握蒙古语,并不像一个汉族人在大学英语系学成了英语。需要的时候用英语跟别人交流。但英语不在他心里。对我来说,蒙古语在心的底下,汉语在上边。
我掌握的蒙古语是感性的,可以摸到、看到、听到、闻到。有的作家写作使用的一些词汇,比如“必须”“问题”“一定要”,我觉得这都不是文学语言。蒙古族牧民不说这样的话。语言像路标一样在你心里躺着,告诉你不要用这个词,要用那个词。这样的区别就是作家与作家的区别。有人自称是蒙古族作家,却不懂蒙古语。他写得再好,也写不出草原的本色和蒙古民族的质地。
汪政:我们今天谈得最多的是语言,你的作品给我们读者启发,特别是小朋友。对小朋友来说,有助于他们建立起语言与生活的良好关系,对成人们来说,它让我们思考如何重建人与语言的关系,重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本质上说,关系到我们的文化态度和生活态度。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你的语言态度。当语言动起来的时候,世界也动起来,人也动起来。我们的语言生活困难重重,不能用语言跟社会,跟自然,跟人,跟我们自己建立起丰富的联系,不能用语言发现世界、表达生活。但我们好像对此都麻木了。
鲍尔吉·原野:谢谢汪老师,我赞成您所说的,一个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里重新建立人和语言的关系,重新建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我愿意为此努力。
我特别高兴的是,汪老师把这些话送给了正在读书的小朋友们,让他们珍惜语言。向好的文学作品学习。
汪政: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有其他语系背景的作家,他们能带给汉语很多新鲜的东西,比如阿来、张承志,他们的语言都有很独特的气质。
鲍尔吉·原野:也许他们自己没有察觉,但是确实很特别。
汪政:因此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样带有异质性的作家,对汉语有外部的观察,再进入其中,跟我们一开始就在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谢你们为汉语作出的贡献。
鲍尔吉·原野:谢谢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