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良知
作者:何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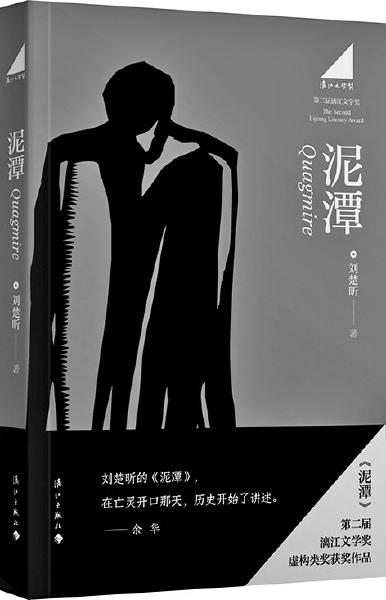
对《泥潭》(漓江出版社)而言,不能不提的是,在未被读者完整地阅读前——还只是有限剧透的片段和余华等小说家和编辑家的转述,《泥潭》作者“刘楚昕的故事”已经在网络舆论场和大众传媒流传,或者干脆说拥有了流量。
这是刘楚昕的奇幻漂流——“有故事的人”刘楚昕比“讲故事的人”小说家刘楚昕提前降临。接着,更大范围的、不同阅读预期的读者评价完整版的《泥潭》,对刘楚昕来说,将是一场硬仗。
文学读者肯定希望,凭借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泥潭》,当“有故事的人”刘楚昕那波流量过去,作为“讲故事的人”小说家刘楚昕依然是小说家。在小说这个庞大的家族中,许多也是有前缀的,比如通俗小说、类型小说、网络小说、非虚构小说等等。
如果要真的给《泥潭》认祖归宗,它是一部“现代”小说。在世界小说传统中,现代小说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以降的欧洲小说,尤其是以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为起点的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它的起点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样比,无非强调刘楚昕的写作是属于一个庞大的小说传统上的、一个如果要加前缀可以加“现代”的小说传统。
事实上,今天许多小说家并不是像刘楚昕一样,继承的是这一笔现代小说的技术和精神遗产。从常识看,《泥潭》不是没有其他更为通行的中国当代小说道路。比如地方志式的。刘楚昕几乎已经接近这条道路。他在后记里说,“翻阅家乡荆州地方志”,“发现清末时期充满了冲突:满汉、革命党和清政府……”比如家族寻根式的,比如重述近代革命史。应该说,无论是地方志式的、家族寻根式的,还是重述革命式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都给刘楚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模板。
荆州只是《泥潭》的前景和背景、外景和内景,而不是它的全部。刘楚昕更关心的是让他所选定这个文学地标。
我们看地方志式的、家族寻根式的和重述革命式的长篇小说,当小说成为一般知识,成为小历史,成为“史余”,小说虚构、想象和重构世界以及勘探生命限度和人性尺度的能量都会衰减。《泥潭》虚构、想象和重构的世界是浑浊幽冥的“泥潭期”,以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良知为人性尺度,勘探个体的生命限度。
小说第一部分八旗子弟、左都统恒龄之子恒丰在开启“亡灵”奇幻漂流之前,经历了王朝和家的崩毁。他没有成为更强大、更有反思能力,内心丰盈浩大、向上生长的人,而是施暴比他更无力更需要庇护的弱者。
小说第二部分转场写革命党人关仲卿的疯癫和治愈。他是旧中国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一个“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人。他传奇性的革命生涯是一个有自知和良知的新人在世界和中国的奇幻漂流。第三部分以书信的方式接入楚卿家族往事和私人情爱过往,以及恒妤、玉楼、格蕾丝等的生命片段,这些或多或少不幸的女性,她们的奇幻漂流,最后都各有归处,且是小说中闪烁着人性和生命光泽的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相信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良知。
刘楚昕从写一部单纯的“史诗般的小说”起意,到现在经过十数年的改写和复写,客观上造成文体的重叠和延宕。回到现代小说传统,这种分身和合体、重叠和延宕,正接近健康和生机的长篇小说应该具有的众且不同的声部的争辩和对话。